内容提要:继“后知青小说”之后,《春山谣》在叙事视野、小说结构与美学风格上,突破了以 往知青小说的写作范式。张柠通过春山岭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揭示出异乡与原乡之间的辩证关 系;通过顾秋林这个“情感型”人物,提出了“刺猬的幸福”这一艺术理想;通过“诗入小说” 以及对劳动与歌唱这两种经验的鲜活呈现,创造出强弱起伏的美学节拍,为长篇叙事艺术应该如 何创新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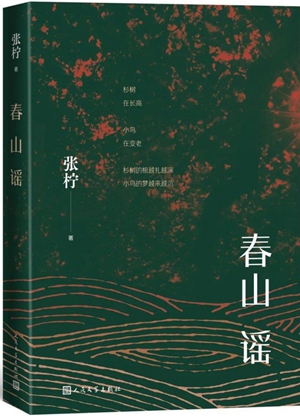
《春山谣》,张柠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异乡与原乡:分成两半的春山岭
《春山谣》是张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首先,这是一部讲述“上山下乡”的知青小说。1960年代就出现了《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等以知青开拓边疆为题材的小说,笔调上积极昂扬,将知青塑造成为自愿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开荒拓土的英雄。同时也有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这样展现知青灰暗痛苦情绪的刺耳声音,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十七年”小说政治化、概念化、工具化的创作倾向。以“手抄本”形式在“文革”期间流传的《波动》,写于1974年,因为全新的创作手法而成为后来知青小说的先声。1970年代末,卢新华因为《伤痕》一举成名。小说对“上山下乡”生活阴暗面的描写,对知青伤痕的暴露,推动知青小说的写作走向了批判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知青小说渐渐地走出了情绪化的“伤痕”,走入了深沉的“反思”。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艺术特色更加突出,提出的知青回乡以及回乡后怎么办的问题,更加尖锐。韩少功、路遥、李锐、王安忆、铁凝、张抗抗,他们前期的中短篇小说大量取材于知青的经历。1980年代,知青小说领域诞生了诸多成熟的作品,比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黑骏马》,阿城的“三王”,或悠扬或浪漫,或朴拙或玄奥,各成风格。总体而言,1980年代的知青小说有浓郁的抒情气质和历史反思精神,“青春无悔”的自我感动出现而后崩溃,创作倾向从昂扬走向沉郁。到了1990年代,韩少功、李锐、王安忆这些在1980年代活跃的知青作家,渐渐脱离了对知青题材的依赖,走向更宽阔的写作境界。同时,对于知青故事的新写法出现了。一种写法是以回忆录或非虚构的形式,突破过往写作的禁忌,正视知青逃亡等敏感历史问题,比如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另一种以王小波为代表,他的《黄金时代》用反讽颠覆抒情,用智性补充灵性,以裸露戳破伪饰。知青小说的传统得以深化。进入21世纪之后,知青们已经衰老。非知青出身的后代作家以更加抽离、冷静的立场,重新进入“上山下乡”的历史现场,这就是“后知青小说”的兴起。比如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李洱的《鬼子进村》、刘醒龙的《大树还小》等等。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知青小说,没有刊物、口号、理论,没有美学阵地,加之知青作家是文学的“散户”,美学追求的差异性很大,所以没有形成煊赫一时的流派。但知青作为一类文学人物,“上山下乡”作为一段集体记忆,一直在新时期文学的各个流派里被反复书写,形成了一条写作资源的“暗传统”。
《春山谣》诞生于“后知青小说”之后,和“后知青小说”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相似性可以从两方面谈。第一,和“后知青小说”一样,《春山谣》的写作不是出于“伤痕”与“反思”。在知青出身的作家眼里,他们是“浩劫”之后的幸存者,所以他们刚走出废墟,就坐在废墟边上开始了回忆。这种幸存者的回忆,有一种不吐不快、沉冤得雪的倾向,免不了对已逝青春的浪漫凭吊、对文化灾难的控诉、一种生命被安排和被抛掷的虚无感。而《春山谣》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更加抽离和中立,不是“诉苦”的语调,而是“告诉”的语调。“文革”不再作为一场生活的“浩劫”被书写,而是作为生活的一次“变奏”被书写。由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被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生活细节,解放了出来。第二,过去的知青小说,作者无一例外都是知青身份,是“上山下乡”的亲历者。这种身份容易让写故事变成写“回忆录”与“血泪史”。对于亲历者来说,知青小说怎么写的问题,其实是他们如何回忆和定义“文革”的问题。一方面是怎么定义“文革”这一段大历史,另一方面是怎么定义“文革”中个人的小青春。作家对前者的态度与当时的中央文件高度一致,倾向于否定性的、历史理性的;对个人青春的判断则相反,倾向于肯定性的、感伤主义的。两种矛盾的情感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这批知青小说情感立场上的缠绕、暧昧与龃龉。和“后知青小说”相类似,《春山谣》不存在这种内部的情感撕裂。因为张柠的身份并不是下乡的知青,而是在乡下迎接知青的孩子,是一个乡村立场上的旁观者。亲历者主观抒怀的倾向,被旁观者冷静观察的倾向取代,第一人称的“热抒情”被第三人称的“冷抒情”取代。故事的取景框因此放大了,不再是盯着某个人微小表情和微小心思的特写镜头,而是一系列包含多人关系的远景、中景镜头。我们不仅能从小处着眼于知青的情绪,还可以从大处着眼于农民与市民、春山岭与上海滩、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心灵空间与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空间,个人的生命体验与人群的集体经验,下乡知青、公社干部、林场农民的生活与命运,在《春山谣》中得到了全景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春山谣》拓宽了知青小说的艺术表现范围。
除此之外,《春山谣》的结构也溢出了知青小说“暗传统”提供的范式。《春山谣》是一个“双结构”的故事。从来自上海的知青的角度看,《春山谣》是一个团圆的结构:从“散”(离家)到“聚”(归家)。知青们先是被迫离开家乡上海,来到春山岭之后,经受了饥饿、孤独、失恋、失去自由的种种考验,最终成功返回家乡上海,回到了亲密的家人、充足的物质、时髦的消遣和光明的未来那里。《春山谣》的特殊之处在于,小说还隐含着一个乡土立场上的反面结构——反团圆的结构:从“聚”到“散”。在春山岭的眼中,知青们先是热热闹闹来到了它的身边,与它的空间和空间中的人产生了种种政治的、利益的、情感的联系,渐渐聚合成为一个临时的共同体,最后又一个个从共同体中掉头走掉,空留下一座寂寞的春山岭。
为什么两种结构拧在一个故事里,又没有产生冲突?这需要我们将知青们分成两类、将故事分为两种版本来看待。一类是陆伊、程南英这些盼望着通过上大学逃离春山岭的知青。在他们眼中,春山岭是一个异乡,一个囚牢,一个炼狱。他们所爱的家人、城市和小资生活,都不在春山岭。所以,返回上海的结局,对于他们是一种解脱。他们活在从“离家”到“归家”的喜剧版本的故事里。另一类知青是主人公顾秋林,他是知青当中的一个异数。对他来说,春山岭并不是囚牢,更不是一个炼狱。他从没有表现出对于春山岭的厌恶与憎恨,相反,他在春山岭活得适然而幸福。因为他心爱的手风琴、诗歌和女人,都在春山岭。其他人都没有在春山岭扎下根,只有他的青春在春山岭落地生根了,不但生根,而且发芽了、开花了。
包括陆伊在内的其他知青,始终带着某种自私心理,不愿意向春山岭交付出自己的私有物,始终是共同体边缘的游荡者,随时准备着从不情愿的命运当中逃走,逃回城市的布尔乔亚秩序之中。只有顾秋林身上带着一种流浪的“吉普赛人”气质,他没太有“个人所有权”的概念。只有他将私人历史彻底交付了出来,融入了春山岭的公共历史。所以对顾秋林来说,离开春山岭,就是从春山岭的统一体当中分离出去,就是由“聚”到“散”。这么看,这部小说其实只有两个主要人物:顾秋林和春山岭(正如李白和敬亭山)。故事中,他们相遇,热恋,然后分离。这无疑是一个悲剧。
由于这双重结构,我们看到了一个分成了两半的春山岭:一方面,是知青们的异乡——“我替你诅咒荒野和污泥,/春山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另一方面,又是顾秋林的原乡——“我替你感谢草地和山花,/春山岭收留了我们的心”。这两句诗里面,装的是异乡与原乡的辩证法。
二、刺猬的幸福
我们还可以换个视角,谈谈在张柠的个人创作史中,《春山谣》的位置和独特性。从叙述的历史时段和人物代际来看,《春山谣》可以说是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城记》的父辈篇。《春山谣》的主人公顾秋林,正是《三城记》主人公顾明笛的大伯。这是一群1970年代的年轻人。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依旧可以捕捉到《三城记》的种种主题:个人青春与时代遭际的关系、肉体归宿与精神走向的分离、爱的匮乏与满足、主体的受困与突围、活着的心和奄奄一息的心。
张柠曾在文章《纯文学的优势在哪里?》一文中,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总结阐释过心目中文学艺术的三个考量标准:“1.内容的重要性(人类或社会责任),2.情感的真诚性(道德或情感态度),3.表达的艺术性(个人艺术才华)。”我认为,《三城记》的写作尤其突出了排在第一项的“内容的重要性”,表现为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他有意将顾明笛当作一个美学的、精神分析的、人类学的“新鲜样本”来观察和表现,他要在顾明笛身上望、闻、问、切,由此摸索人物所处时代全新的病症。到了《春山谣》,作者对内容重要性的要求依旧在,写“出了问题的历史中出了问题的人”,依旧是首要的艺术目标;但与此同时,第二项标准——“情感的真诚性”,在整体叙事当中凸显了出来,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完成。
什么是“情感的真诚性”?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们不如通过对人物的分析来探讨一下。《春山谣》当中的人物,不是顾明笛那种头脑发达的人物,而是偏重情感的人物。在西方文学史上,有两种重要的人物类型。一类是“情感型”人物,一类是“头脑型”人物。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可以说一类是“刺猬型人物”,一类是“狐狸型人物”。“情感型”人物(阿喀琉斯、力士参孙、堂吉诃德、庞大固埃)出现得更早一点,“头脑型”人物(哈姆雷特、毕巧林、伊凡•卡拉马佐夫)出现得更晚一点。启蒙运动差不多刚好处在两种人物的过渡带上,促成了文学人物从感性直觉到理性怀疑、从内分泌系统紊乱到神经系统抽搐的转型。“情感型”人物往往肉体与精神的动作是统一的,想爱就求爱,想生气就愤怒,想大战风车就冲上去。启蒙之后,这种蒙昧而幸福的“统一性”(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被打破了,敢于动用自己理性的“头脑型”人物轮番上场。在“头脑型”人物看来,“情感型”人物是简单的,阿喀琉斯之于哈姆雷特是简单的,李逵之于宋江是简单的,张飞之于刘备是简单的。但“头脑型”人物的问题是,他们知行不合一,想逃避责任偏偏又拿起了复仇之剑(哈姆雷特),想爱的时候偏偏要诅咒(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想暴怒的时候偏偏一副惊人冷静的面孔(海明威笔下的杀手)。灵与肉谈不拢了,心和脚走向不同的方向,甚至精神内部也产生了分裂,一会儿自认为是天使、一会儿又咬定自己是魔鬼(拉斯科尔尼科夫)。
“情感型”和“头脑型”这两种人物,前一种统一、简单、笃定,后一种分裂、复杂、游移不定。哪一种人物更具“情感的真诚性”?我想,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答案。对于具有古典美学倾向的作家来说,知行合一的、精神统一的“情感型”人物,可能更符合“情感的真诚性”要求。而对于比如昆德拉这样钟爱现代美学的作家来说,“情感的真诚性”可能根本不重要,甚至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会认为“真实”比“真诚”更重要,分裂、复杂、游移不定的头脑型人物才是“真实”的,统一、简单、笃定的人,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主观理想;头脑的知识比情感的直觉更重要。米兰•昆德拉甚至表示,“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想要通过知识和智慧来改造疲态尽显的现代小说。这个问题牵扯到现代以来小说美学的分野、哲学的演变,难以说清,只好按下不表。回到文本,我们关心的是,张柠的答案是什么?什么才是他心目中的“情感的真诚性”?还是得回到故事当中去发现。
顾秋林这一批1970年代的年轻人,个个都是“情感型”人物吗?在故事的一开始,可以说是的。他们刚来到春山岭的时候,确实统一、简单、笃定,对春山岭的生活和来到春山岭的安排没有什么质疑,更不要说抵抗。很多陆伊这样的知识青年,主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受洗”仪式。为达到灵魂的净化,虔诚地表示要“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顾秋林在写给陆伊的信中这样表白:“此刻,我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给你写信,对你诉说,思念着你……紧紧握住你的双手!致以革命敬礼!祝你进步,快乐!”用语用词,既有古典爱情的纯真,又有革命爱情的直白,属于典型的“情感型”修辞。他们不像21世纪的顾明笛,不会陷入理性的头脑风暴,陷入怀疑、游移和恍神。此外,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身体无一不是活跃的、好动的、七情六欲的,不会被抽象的概念五花大绑,动弹不得。
顾明笛和顾秋林这两个人物对应着两个时代:“富裕性压抑”的时代(市场经济时代)和“匮乏性压抑”的时代(计划经济时代)。顾明笛就是“富裕性压抑”时代的产物。饮食与男女的富足,让他的身体处在“满足性麻木”之中。一方面,神经系统的高度发达,让他为形而上的问题深深着迷。同时,身体的颓废主义、器官的休眠策略和激素的衰退,又使他产生了经常性的厌倦和沮丧,这就是“富裕性压抑”。顾明笛的解决方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动起来,去往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圈层漫游,去沙漠冒险、去田地劳动,重新激活休眠的身体、衰竭的器官,进而重新激活休眠的爱。
顾秋林他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原本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城市青年,被迫来到吃不饱、穿不暖、没人爱的异乡农村。由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紧张的物质资源以及禁欲的集体主义文化,他们的身体长期处于饥饿的、匮乏的状态,非但不是休眠的,反而是冲撞的、贪婪的、随时准备喷发的。情感的火山整日运动,时不时引发肉体的激进主义行为:打斗、自杀、偷情、咒骂、强吻。对于顾秋林他们来说,需要解决的是由“匮乏性压抑”带来的“剩余能量的暴力”。他们的办法与顾明笛解决“富裕性压抑”的办法正好相反:静下来。
首先,第一步,通过吃饱饭,先让翻腾的胃静下来。第二步,通过肉体和精神的恋爱,让沸腾的欲望静下来。然而,恋爱总有离合悲欢,此事古难全。这时怎么疏解心中郁积的爱欲?有更高级的办法——像顾秋林一样,通过艺术,也就是唱歌、写诗等审美活动,将自己不能正常释放出来的剩余能量,浪费在对于美的享受当中,从而曲折地化解“剩余能量的暴力”。能量不足(静)—补充能量(动),这是“头脑型”人物的自救方案。能量郁积(动)—能量消耗(静),这是“情感型”人物的自救方案。
到了故事的后半段,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身体长期处于艰苦的劳动和饥饿之中,爱欲又难以得到满足,静不下来的知青们,渐渐从对命运蒙昧的服从中苏醒了过来。他们意识到春山岭三个字蕴含的残酷性,意识到被“动员”的人生不是他们想要的人生。生活的艰苦,“剩余能量的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他们的头脑。尤其是推荐上大学的消息传到春山岭之后,知青们像是等到了离开囚牢和炼狱的救命稻草。于是,他们开始“分心”了,开始“走神”了,开始“阳奉阴违”。结果,他们从“情感型”人物,一个个转变成为怀疑、游移和恍神的“头脑型”人物。个中代表,就是程南英。
程南英想通过表里不一的“表演”来获得上大学的资格。这是小说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情节。结果事与愿违,农场将程南英当作扎根农村的正面典型来宣传,枉费了她的精心设计。被迫留守春山岭的程南英,最后精神失常,转而发展成为重度“头脑型”人物。可以说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丢了健康性命。其他人也不同程度上变成了为个人利益盘算的“头脑型”人物,只是没有像程南英一样走火入魔。相比之下,只有一个人,自始至终是统一、简单、笃定的“情感型”人物:顾秋林。只有顾秋林没有被知青之间的明争暗斗污染,没有被男女之间的爱而不得摧毁。相反,通过艺术——手风琴、歌唱和诗,他化解了知青身上由那个特殊时代所强加的“匮乏性压抑”。
通观故事里主要人物的结局,顾秋林属于很凄惨的一个——最晚离开春山岭,终生远离爱人,生活贫困,最后因为心梗早逝。然而,张柠却这样描述顾秋林的结局:“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只有顾秋林没有变。他生活着,爱着,写着爱的颂歌。这个表面上沉默寡言,生活似乎了无生趣的男人,内心却总是被巨大的幸福所充斥。”我认为,顾秋林所拥有的“巨大的幸福”,是专属于“情感型”人物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终成眷属与阖家团聚,不是五花马和千金裘,总之,不是其他知青苦苦追求的“世俗的幸福”,而是安德烈公爵的幸福、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的幸福、万卡的幸福。这种幸福与财富的多少、权势的得失、情爱的去留无关。这种幸福是精神的笃定、道德的纯洁、良知的无缺带来的。这是一种“精神愚者”的幸福,是“刺猬的幸福”。
通过书写一个“情感型”(“刺猬型”)人物经受住心灵的考验最终获得了“刺猬的幸福”,张柠回答了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他心目中的“情感的真诚性”?那就是写出“刺猬的幸福”:让统一、简单、笃定的心灵,得以在统一、简单、笃定当中善终。
与“刺猬的幸福”对应的是“狐狸的不幸”。那些怀疑、多思的头脑巨人和行动矮子,那些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往往无法得到内心的安宁和生活的圆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里,狐狸多,刺猬少。写“狐狸的不幸”太多太多,路翎笔下的蒋纯祖,王蒙笔下的倪吾诚,王朔笔下的马林生,李洱笔下的应物兄,《三城记》当中的顾明笛等等。他们或东方或西方、或执拗或分裂、或清晰或混乱的思想观念,压垮了他们的精神天平。相反,写“刺猬的幸福”的故事,实在很少。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刘恒笔下的张大民,阿来笔下的傻子土司……屈指可数,现在可以再算上一个顾秋林。
一个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作家们的笔下,一种艺术上高度整合的写作——“狐狸的幸福”,存在吗?一个分裂、复杂、游移不定的人,在统一、简单、笃定的结局中善终,这样的故事存在吗?换句话说,一个内心与外部世界处于冲突状态的人,最终他的内心可能与世界达成和解吗?这已经涉及到现代人心灵困境与现代小说艺术任务之间的关系了。卢卡奇说,曾经有一部作品,“作为一种综合尝试”,几乎写出了“狐狸的幸福”,那就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小说的主题是“难以解决的、由体验的理想所引导的个人与具体社会现实的和解”。总之,挑战写“狐狸的幸福”,是艺术上的奥德修斯归乡之旅,是作家心灵的一场巨大的冒险。技术上圆熟、心灵却很保守封闭的作家,是上不了奥德修斯之船的。
三、劳动与歌唱:《春山谣》的强弱拍
还剩“表达的艺术性”这一项要求,以赛亚•柏林排在三项艺术准则的最后,这也符合伟大作品的现实。托尔斯泰自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复活》,恰恰是艺术才华上最收敛、技巧上最坚硬的;莎士比亚的问题也在技术上——根据托尔斯泰的批评——他不用“活人”的语言说话,缺乏“分寸感”,没有达到“平衡”“和谐”的艺术要求;同样的批评也可以拿来扣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头上,他的全部作品都缺乏古典美学的分寸与节制,但艺术技巧确实也从来不是他最重视的,他关心“问题的重要性”,胜过关心“谈问题的修辞的重要性”。
《三城记》的故事就给人这样一种感受。小说关心“问题的重要性”,胜过关心“谈问题的修辞的重要性”,在情节排布、叙事节奏、故事结构上考虑得并不多。故事是随人物精神生活的流向朝前自由流动的。但是,到了《春山谣》的写作,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作者在表达技巧方面的考虑增加了。形式上的设计更加充分,“内容”“情感”“表达”,三者得到了一种考量上的平衡。
《春山谣》最为独特的形式,就是“诗入小说”。古典白话小说有“有诗为证”的写法。这与“以诗证史”——以虚构佐证历史现实的“史传”传统有关。在体现虚构与现实的等级关系的同时,“有诗为证”还体现了古代文学中诗歌与小说的等级关系,诗歌是更有权威、更具流传价值的体裁。《春山谣》中顾秋林的诗歌,一定程度上有“证史”功能,但并不是为了印证知青们的劳动生活史,而是为了印证顾秋林的心灵演变史——兴奋、思索、煎熬、和解等等变化。从印证心灵史的意义上来看,《春山谣》与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写法更接近。
《春山谣》是顾秋林诗集的名字,收有诗歌五十余首,在小说中总共摘取、呈现了8首。这8首诗像一个谜底附录在故事的结尾,等待着读者最后揭开。怎么写这8首诗歌?用怎样的艺术手法、意象体系、政治立场、节拍节奏,才能符合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青年?选取什么内容和笔法来写,才能让诗歌与叙事部分构成涵盖、对话、启示等等的关系?这都是创作当中的难题。
从最后呈现的效果来看,我认为诗集《春山谣》和小说《春山谣》,的确构成了一种融合的、亲密的、互动的关系。第一,诗集当中的诗形态各异,展现了顾秋林“上山下乡”过程中多面的情与思。有稚拙的,稚拙中有巧思(《杉树林里的小鸟》);有调皮直白的,直白里有反讽(《德宏师傅你好!》);有晦涩的,晦涩里有单纯的痛苦(《青蛙之死》);还有抒情的,抒情里有悠长的哲思(《献诗》)。我感觉,诗歌小篇幅当中展现的顾秋林,比小说中大篇幅展现的顾秋林更加立体丰满。诗的顾秋林作为一个详实的注释,丰富了小说的顾秋林。这句话反过来表述,依旧能成立。
第二,诗集《春山谣》用凝练的形式,将小说中的重大主题“加深”了一遍。透过诗歌,我们发现这些主题是成双成对的,构成了一组组经验的“强弱项”:树与鸟、污泥与山花、知青的身与梦、革命与日常、异乡与家乡、劳动与歌唱、民间世界与城市世界、工农阶级与知识分子阶级。在小说《春山谣》的世界里,前一种经验总是在压倒后一种经验:树的经验压倒了鸟的经验(“杉树的根越扎越深/小鸟的梦越来越轻”);异乡的经验摧毁了家乡的经验(“我在春山下的小屋里昏睡,/长河尽头的家乡,在梦里流淌。”);劳动的经验压迫着歌唱的经验(“汗珠是从身体里/涌出来的吗?/它为什么不是眼泪?/赤裸的背脊里/流出苦涩。”)。
这些经验的“强弱项”,构成了《春山谣》的美学节拍:由“强弱拍”构成的偶数拍。这种以“生/死”为一个轮回的偶数拍,是自然节奏的“原型”,充满完成性、圆满感与东方意识。与此同时,这些“强弱拍”,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史的节拍。强拍是政治的、国家的、一体化的节拍,弱拍是非政治的、个人的、多元化的节拍,强拍一直在压抑着弱拍。洪子诚有更加周全的表述 :“一种(力量)是努力使文学更多摆脱同其他实践活动的原初联系,摆脱其对其他活动的依附地位,另一种力量则要更加强这种联系,并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新的联系、依附方式。从实际情况看,前者的力量是微弱的,始终处于被压抑、挤迫的位置上。”可以说,是“前二十七年”社会历史的节拍,决定了《春山谣》的美学节拍。
在《春山谣》的种种“强弱拍”中,“劳动”与“歌唱”这一组,是关系最复杂、最紧张、最纠结的一组。首先谈“劳动”。让知青下乡,在当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这一政治任务的核心要求就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化”是这样一个过程:知青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形成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最终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从大都市上海来到穷乡僻壤的知青们来说,“劳动化”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他们要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变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劳动人民”,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把“私心”练就成“红心”。所以,对知青而言,劳动是一种强制,泥土是陌生人,汗水和污渍是一种“丑”。但是,在春山岭世代耕作的农民眼中,劳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是一种自然行为,泥土是亲人,汗水和污渍是一种“自然美”。于是,《春山谣》写出了两种劳动,一是“政治化的劳动”(陆伊的劳动),二是“自然的劳动”(游德善的劳动)。
“歌唱”与“劳动”息息相关,比如劳动号子、船工号子,唱起来是为了给劳动以节奏、以效率、以团结的力量。这种“劳动号子”的变体,就是“革命歌曲”。“劳动号子”是号召农民用铁锹有节奏、讲团结地攻击泥土或水面,“革命歌曲”则是号召农民用铁锹有节奏、讲团结地攻击敌人。(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一种“暴力的劳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歌唱”与“劳动”对立,比如田间地头的黄色小调,陕北的信天游,唱出来是要教人松筋软骨的。
在《春山谣》当中,同时存在着两种歌唱。一种是促进劳动的歌唱——“革命歌曲”的歌唱。比如《红太阳光芒照春山》《“九大”路线放光芒》《毛泽东思想放光芒》《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还有样板戏《红灯记》当中的《痛说革命家史》:“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我跟你前进绝不彷徨!”这种歌曲铿锵、果决、有力的节拍,与劳动的节拍是一致的。
《春山谣》当中另一种歌唱,是消遣的歌唱 ——“爱情歌曲”的歌唱。“天上起云一坨坨,哪个山包不通河,哪个男人不想女,哪个女人不想哥。”(春天耘田仪式的山歌)“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喜盈门,人家夫妻团团圆,我夫喜良他修长城。”(《孟姜女》)还有民歌直接带给了知青们性启蒙:“开门见哥浑身冰呀冰冰凉,一把搂住啊我的哥哥在怀抱。”(《三更月》)“伸手那个要把妹呀妹妹摸。”(《十八摸》)这些歌唱不遵循劳动那重复的、强弱相间的二拍子,而是悠扬玩转,一唱三叹,会破坏劳动的身体节律,从而让人的肌肉和情绪放松下来。
有趣的是,这些让人心魂萎靡、不事劳动的爱情歌曲,并不是知青们“自带”的,相反,是春山岭这样的乡土社会里土生土长的“民间特产”,是一种民间的抒情。这种民间抒情,“甚至就是对肉体禁忌的解放,是对肉体长期受到社会、自然压迫的一种补偿。暴力和色情成分是肉体解放的两个重要因素”。 相比于循规蹈矩的上海滩(知识分子文化),严肃古板的北京(官方文化),泥里面长出来的春山岭(民间文化)反而才是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
“上山下乡”的本意,是让有问题的知识青年们,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因为“农村是座大学校,贫下中农是老师”,结果——《春山谣》向我们揭示出了当时历史的一种可能性:这些老师们正经事(劳动、吃苦、为人民服务)没有教会,反倒教会了很多被禁忌的事情(歌唱、性、自由恋爱)。原本,官方想要借助民间的力量“驯服”知识分子,结果,知识分子却被民间那种深厚的、狂欢的、自由的文化给“逆向启蒙”了。农村的生活确实“改造”了知青们,但这种“改造”和当初作为一场文化运动来设想的“改造”已经截然不同。因为改造他们的不是预想中艰苦的劳动,而是悠扬的、动人的歌唱。
劳动是现实原则的产物,压抑着生命的力比多;歌唱则是快乐原则的产物,帮助我们体验到了生命的自由。快乐的歌唱改造了知青们,尤其改造了顾秋林。歌唱让爱而不得的他写出了诗集《春山谣》;歌唱让漂泊他乡的他找到了“心灵的原乡”;歌唱让穷困潦倒的他得到了珍贵的“刺猬的幸福”。劳动是重要的,《安娜•卡列琳娜》当中的列文、《三城记》当中的顾明笛,都是依靠必要的劳动来拯救自己的。然而,当强制性的劳动让我们奄奄一息的时候,《春山谣》启示我们:不要忘记生命内部歌唱的冲动——“这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