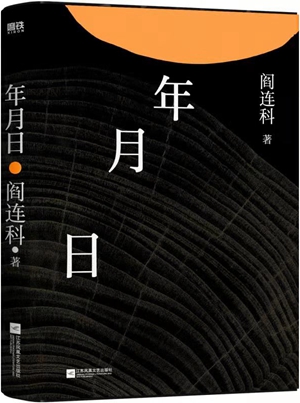
《年月日》,阎连科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没有什么比回忆写作的写作更为温暖和忧伤,一如残迈的老人回忆年轻时的某个生日样。
到1996年秋,我已经有五年没有直腰走过路,却也没有真正驼背躬身弯过腰,那半畸半废的腰病和永远头晕、耳鸣的颈椎病,使我终年都在北方的几个省份跑着求医和问药,又在暗自落泪的缝隙里,不断地趴在床上写作。也就在这年秋,在偶然对偶然的帮助中,我腰椎、颈椎的疾病明显轻缓和舒适,有机会在西安远郊玉米地的空寂里,沿着一条小路一直一直地走,朝着旷荒无人的虚地去,感到人可以端直地走路是多么地幸运和愉悦,几乎是一种生命的美。落日在前面。野草在脚下。寂静在我四周响出噼里啪啦声。我正走着不知为何突然收住了脚。突然在一个深邃死寂的片刻间,脑子里门洞大开地闪出了一个
光炫来——
“如果人类的祭日到来了,世界上只还有一个人和一粒种子会是什么样?”
我被这个念头震住了,甚至有些惊慌和骇然。在这一瞬间,我看见黄昏的落日如朝阳一样明亮而透彻,在日光中飞舞的静谧带着甜味宛若舞蹈中的红绸子、蓝绸子。
我开始相信艾略特说的“灵视”了。我看到神恩如微型闪电样,在我眼前突然一亮走后,把它的光影留将下来了。如此我慌忙转过身,怔了怔,快步由寂静朝着人烟稠密的住处去,觉得我不再是一个残人和畸物,而是一个比谁都健康、比谁都更有生命力的人。回到住处收拾了行李去和恩医告别握了手,来日急急乘火车回到了北京的家。第三天,我一早仰躺在由中国残联工厂为我特意设计制作的椅架间,面向天空,胳膊双举,开始在横架头顶的活动板上举笔写作这部《年月日》。
一稿而就的一周后,我把这部小说寄给了《收获》杂志社。之后关于这部小说的阅读和热闹,使我对写作开始有了宗教般的“迷信”和神秘感—— 我开始相信好文学一定是一个人生命驿站的写字桌;相信文学的神至、神视和灵之光;相信神来时,文学的黑夜决然是种朝阳色。于是在日后,我每天都在握笔等待着神至、神视那一刻,像等着一间漆黑的屋里猛然透进一丝光;等着挡在面前的一堵墙,轰然塌下去,使我看见有条发光的路,一直一直通向遥远、伸到地平线对岸的天那边。然而那漫漫等待中的神视和灵光,一天天和一年年,它很少、很少再来过,如一个四十岁的人等不到二十岁的生日样;一个苍苍白发的人,吃尽了黑豆也等不到一头乌发来。就这么在漫漫默默的等待中,疾病又陪我过了二十几年去,虽然每天每年的苦等都落空,可我依然相信神视它还会来,即便在黑夜来了也是朝阳色,如同一个每天躺在病床上的人,天长地久地等不到花圈才是生命的美。
《年月日》是不是生命中一束干枯的花朵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曾经在虚荒死寂中光顾过我,让我相信虔诚握笔等待的人,终会在黑夜中再次看见灵至神视那束光。
2021年5月21日 北京
(《年月日》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