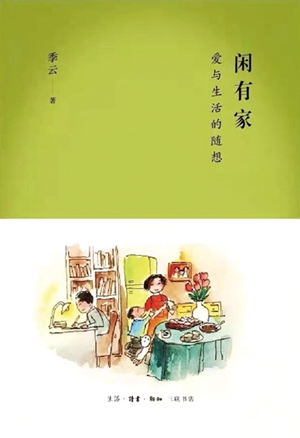
《闲有家》,季云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季云的随笔集《闲有家》多少带点传奇的味道。“闲有家”出典于《易经》,原义是插上门闩,就可以守护一个家院的安全和温馨,引申开来就有了“正家”与“齐家”的意思,也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齐家”的思想。《闲有家》的基本内容,讲述的是“家”的方方面面:老家的族谱、青灯儿时的生活、自己上学的坎坷、做母亲育儿的辛劳、孝敬老人的悉心、下厨房做美食的点点滴滴,等等,都是带着个人的生活体验,非常真实地进行讲述。这些都是一点也不掺假的“非虚构”叙事。
这部书的一个很显著的动情点,是作者在家庭日常生活叙事中,将自己作为女儿、儿媳、妻子、母亲、婆婆、大姐等多重“角色”,用“正”己与“齐”己的伦理和人性诉求,描述并塑造着自我形象。也许,这些角色的自叙在作者是随意的而并非刻意。然而,散文这种文体的自叙传和自塑性,却很偏执地、毫不隐晦地将作者自己给读者描画、裸现出来了。伦理的、道德的、人性的自我呈现中,季云偏向了传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诸多文化悖论之间,阐释着她的家国思想和家国情怀。这是这部书在思想上另一个显著的魅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齐家之风》《闲有家》《教子婴孩》《家有贤妻》《妻子做主》等作品引经据典,承接传统的家国思想,对“家”与“国”的大伦理关系进行了独特的阐说,她反复告诉读者,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齐家才能治国。她说:“《周易》中‘乾’‘坤’‘家人’‘恒’‘泰’等卦的《易传》,时至今日仍在传递着人类传统的治家之道……有我们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它体现在对老百姓日常生活和言谈举止的规范上。”显然,作者执拗地想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及自己认可的当代妇女人格独立的思想,回归到家庭,回归到普通百姓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她将妇女人格独立的思想,赋予了之于家庭的“女诸葛”“减压器”“警示灯”“平安扣”等(《妻子做主》)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全新内涵。
社会经济急剧的转型、信息时代灯红酒绿的生活节奏,使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现象。鉴于女性被商品化、被欲望化、被物质化的现象,后新时期和新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化与全球化接轨,于是出现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思潮。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既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整合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合理思想内核,从而走向本土理论和实践的文化自觉,是当下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季云在批判性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言说着关于家庭生活叙事中“妻子做主”(季云“女性独立”的概念)的一些女性独立方面的思考,关于养正教育、启蒙教育、家道治理等方面的个人观念,对如何在新世纪家与国大伦理之下重新认识男女平等、如何重新给女性性别身份定位、如何重新在新时代新世纪做“贤妻良母”、如何重新思考女性生存和发展空间等很多问题都有独特见解;作为知识女性、退休的国家公务员,她于此以自己的道德良知,为当下的妇女如何“做自己”立言,这是对中国女性主义的讨论如何引向深入,做出了的回答。于此,《闲有家》的外延意义,值得我们深深地予以思考。
除了表达自己的家国思想和为妇女立言的诉求,季云于文学是“无功利”写作。正如毕飞宇在《闲有家·序言》里所说:“职业作家的写作多多少少都有他的诉求,多多少少都有他的利益。但是,季云的写作真的是日常的,没有排行榜在等待她,没有文学奖在考验她,没有回报在等待她,当然,更没有文学史在折磨她。”我所说的“无功利”写作,自然是指毕飞宇所说的没有种种文学的“光荣”和经济的利益而写作。惟其如此,季云的《闲有家》的写作完全进入到一种自由的王国。季云的“传奇”,也在这一点上充分表现出来。
心无虚荣心的挂碍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人心就会澄明,下笔就是一种纯粹、通透的境界,一种精神书写的绝对自由。用毕飞宇的话说,“季云的笔触是游走的”,是“旅行家”自由而快乐的“游走”。于是,对应在文本的创造上,季云的自由是区别于一般散文家的自由。她既不拘泥于文体的“守正”,又不需考虑文体的“失范”,在她的写作中,什么散文学原理、什么散文的清规戒律、什么艺术方法与技巧等等,都抛掷九霄云外;仅仅靠着素有的文学积累和文字表述的基本功,来自由自在地结撰文本。于是,季云信口开河、跑马无缰、率性而为、我手写我心,散文成了她自由写作的“跑马场”,也是她的文章“破体”的“试验田”。如果给《闲有家》定性其体式,应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尽管《我的四季》有点像忆旧性散文、《坎坷高考路》有点像报告文学、《齐家之风》《闲有家》有点像读书札记、《“简”的境界》《积善之家》有点像杂感……但大体说来,作者所写的这些文章,都可以归类于自由随便、没有定体的文化随笔。
季云的散文创作,与她平素文化知识方面的进德修业密切相关。她平时爱读《易经》《论语》《孟子》、老庄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这使她批判地接受了中国古代先贤的哲学思想,使她的文化随笔具有古典哲学力量的支撑。同时,她还爱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使她写作随笔时,可以自由随便地引录黄庭坚、郭沫若、章太炎、邵力子、张爱玲、汪曾祺、毕淑敏、托尔斯泰等名家名言,来佐证、阐释自己的思想观点。此外,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杂志社做过多年的文字编辑,积累了文字经验,奠定了她散文写作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三方面的厚积,才有《闲有家》必然的薄发。
散文创作除了理智、学养、文字基础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创作机制是激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当季云将“最凡俗的人类情感”升华为抒写家国情怀的激情的时候,她不能自已,必须用文学中的“老年人文体”,包纳、发抒她的激情,进而沉醉且“滋润”她“闲有家”的叙事。我们细细品赏季云的随笔,仿佛能听到一颗赤子之心在字里行间不息的搏动,感觉到她像一位抒情诗人在狂热地咏唱。我想,激情出诗人,激情加思想即演绎为她散文的生命形式,季云写作“一发而不可收”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