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许春樵的作品近年来实现了创作层面的突破,由此前的饱含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作转向对更为浩阔的人性化和审美化的人之生存与命运的观照。这一转折从发表于2016年的中篇小说《麦子熟了》中初见端倪,最新的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不仅延续了人性化、审美化的创作理路,也可视为其创作思路演变后的“完形”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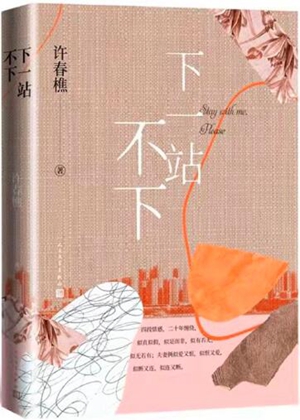
《下一站不下》,许春樵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家许春樵的最新力作《下一站不下》继承和保留了既往小说创作中的优秀基因,又完成了从中篇《麦子熟了》(2016)开始的创作转型,是其创作自我超越、突破后的“完形”之作,在他个人的创作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我们也看到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从道德救世的激昂彻底走向了人性审美的浩阔。这种转变不仅关乎现实主义的题旨、形式、审美风貌、叙事话语的迁移,也关乎创作主体对生活的认知、感受和姿态的转变,更关乎创造者精神结构的自我完善。
一、从“渐变”到“完形”,有迹可循
20世纪90年代初及之后一段时间,秉承着先锋小说的余绪,许春樵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先锋意味的小说,如《季节的景象》《季节的情感》《季节的背影》《谜语》《悬空飞行》《推敲房间》《跟踪》《犯罪嫌疑人》《过客》《礼拜》等,这些小说表现出诗意的恍惚、结构的迷宫、意义的不确定性、黑色幽默、现实的隐喻和形而上的荒诞等诸多先锋性叙事特征。在先锋日渐式微的文学语境中,尽管这些小说拥有相当不错的质地,然而已很难产生大的影响。不过,这并不影响这些先锋意味的小说对于作家本人的创作价值:叙事的改良——经历过先锋叙事历练之后的现实主义叙事,有着更为开阔的胸襟、宽广的视野以及对现实更为透彻的理解。似乎从中篇小说《找人》(1999)开始,作家告别了形式意味较强的现代主义写作,全力开启了开放性包容性的现实主义叙事。我不认为这是作家对市场的妥协,对文学世俗化的认可,恰恰相反,作家以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及时回应变化着的时代和生活。诸多中篇小说《一网无鱼》《生活不可告人》《不许抢劫》《来宝和他的外乡女人》《知识分子》《九月的天空》《你不是城里的女人》《缴枪不杀》……聚焦社会的底层群体、落魄的知识分子或者城乡的官员,构建了现实主义叙事的深度模式,从多个层面回应、揭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各种情状,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对时代、现实的“正面强攻”。只是所谓“强攻”,并没有采取主流的宏大叙事,而是采用了迂回、反讽、批判的个人命运叙事,凸显生命个体在特定时代语境中的生存现状、灵魂异化和精神困境。
无论是早期的先锋叙事,还是稍后的现实主义书写,虽然审美面目迥异,但内在的精神指向有着统一性,即社会转型期人们生存的艰难以及在社会世俗化、市场化的现代性历程中,“发展”伦理和道德伦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生存伦理和知识分子精神伦理之间的尖锐冲突所导致的小说人物内心的撕裂与痛苦。小说人物所反映的时代征候实际上也是创作主体在时代转型期内心焦虑的衍射和对象化。在弗洛姆看来,“人摆脱了束缚他的所有精神权威,获得了自由。但恰恰是这个自由使他孤独焦虑,使他为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体验所击溃”。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成长起来的许春樵(1983年大学中文系毕业),他的精神谱系必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新启蒙的编码和重组,那个年代的道德理想、人文精神、科学理性、人道情怀构成了其精神底色或知识分子品格。而“后新时期”的消费主义、世俗化、金钱拜物教、娱乐至死、文学的边缘化让心怀理想的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思想依凭,被迅速地抛入粗鄙、庸俗、市场化的新的历史情境中,引发了作家主体的焦虑和“存在性”不安。不难想象,许春樵的精神结构和道德理想与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欲望无限膨胀、道德伦理的滑坡是格格不入的,他反复书写20世纪90年代人的故事和命运,以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姿态,试图和现实构成对抗,从而缓解内心的焦虑,同时也是作家救世的“理想”。许春樵曾言:“应当说‘救世’的妄想更为准确些。如果一个时代处于集体无意识的堕落状态,非道德的道德化,反价值的价值化了,拯救就是徒劳的,我们写作的意义在于,虽然徒劳,但我们从没放弃。”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作家对欲望化时代的“堕落”是痛心疾首的,他要像西绪福斯一样对抗生存的荒诞,虽显虚妄,却也是“有意义的徒劳”。
由此,作家的创作多聚焦转型期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关注他们被时代所抛弃的悲戚,聚焦有正义感、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坚守,聚焦官员在利益、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的被腐蚀。中篇小说《找人》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小说讲述了下岗工人老景身患残疾,担心儿子的大学录取被有权势的人给挤占,于是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建议下,背上咸鱼和咸鸭蛋到省城“找人”。“找人”在小说中是实写,其引申义却意味深长,这是中国关系哲学在微观政治与生活领域无处不在的体现。“找人”不仅仅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成为常态,在法治还不完全、不够充分的社会现实中,仍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转型的“失范”期,“找人”可以说更是切中了时代的痛处。小说通过老景的命运揭示了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作家的批判意识和道德正义感是显而易见的。《放下武器》不是寻常的“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它关注的是人与环境、社会的紧张关系,关注的是在官场规则及真相背后主人公郑天良人性的坚守、挣扎、分裂直至毁灭的过程。与一般的官场小说相比,《放下武器》更具有思想深度,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童庆炳和陶东风认为:“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复制现实,它要求以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光束’来烛照现实,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态度。当作家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浊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从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其创作意图就不是表象的现实写作,而是深入现实的底部揭示官场环境对人灵魂的异化。《放下武器》没有像之前的部分“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那样,认同现实的尴尬、丑陋、无奈,并以所谓的“发展”伦理来“分享艰难”,而是充满着道德救世的激昂与义愤,小说没有将郑天良等人进行“自我归罪”,而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权力的运作现场及其生存的土壤。
《男人立正》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写出了在物欲化的现实语境中,陈道生对传统道德伦理、民间信义价值的坚守,小说借人物的诚实、守信、正义来呼唤人们的“道德立正”。在王春林看来:“《男人立正》中,许春樵所强烈关注着的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伦理,而是由经济时代的市场伦理所进一步诱发的恶性伦理。许春樵对于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当下这个时代的理解和认识,又抵达了更深入的一个层面。”确实,到了《男人立正》,许春樵对经济时代的道德伦理严峻现状的考问达到了其叙事的顶点,其道德救世的激昂似乎也抵达了其道德理想主义的高点。到了《酒楼》,小说中道德救世的激昂并没有贯彻到底,而是出现了“折断性叙述”,方维保认为:“当他的叙述进入下半部,在情节历史的中段,则一反常态地腰斩了他过去所坚持的道德理想主义,让道德楷模的形象滑向了其反面。许春樵小说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折断性叙述,既昭示着作家创作的变化,也可能预示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价值选择和叙述姿态的某种转变。”许春樵后面的创作基本印证了这一判断,即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有所淡化,道德救世的激昂开始降温。《屋顶上空的爱情》尽管还延续着作家道德理想主义残存的“妄想”,作为知识分子主人公的郑凡,研究生读的是有关屈原的学术,其导师也是屈原研究的大家,可是在毕业后的生存境遇中,他的道德理想主义面临四面楚歌,终于在物欲化的现实面前化为齑粉。至此,许春樵道德理想主义的写作基本告一段落,从创作层面来说,需要自我超越和突破。
能看得出明显转型和自我突破的是中篇小说《麦子熟了》。许春樵告别了“精神立正”式的文学书写,转向更为浩阔的人性化和审美化的人的生存和命运的观照。王达敏认为:“《麦子熟了》是纯粹人性叙写的审美化小说,与许春樵之前的小说完全不一样。这两年,许春樵跟自己较劲,铆足劲要突破自己、超越自己。《麦子熟了》破壳而出,于不一样中初步实现了他所期待的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小说以“麦子”为主题意象,审美化地展示了麦叶、麦穗、麦苗“乡下人进城”的不同命运,尽管作为自然物的“麦子”在文本中并没有真正出现,但“麦子熟了”的隐喻意义和因“麦子”意象而生的审美意蕴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此后的《月光粉碎》中的“月光”意象,《遍地槐花》中的“槐花”意象延续了这种人性化、审美化的小说理路,并获得了业界的好评。而最新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则是作家创作思路演变后的“完形”之作。
二、以“史”写“情”,走向人性审美的浩阔
《下一站不下》小说中人物的道德理想主义困境仍在,创作主体的精神困惑也没有完全离场,但这些已不是小说叙述关注的重点。小说关注的核心是一个时代的物质史、发展史、生存史背景下“个体”的人的情感史、心灵史和精神史。这是许春樵的叙事抱负和小说创作逻辑的必然。早在写《酒楼》的时候,许春樵的叙事指向已经清晰可辨:“我想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官方的总结大会及相关总结报告是从经济数据和政治目标层面来进行的,但我以为在30年经济史、工业史、物质史之外,应该有一个30年民族精神史、心灵史、情感史的总结。于是,就动手写《酒楼》了。”——我觉得作家真正找到了继“道德救世”“精神立正”之后写作的一条宽广的道路。《酒楼》的“折断性”叙述和后续的《屋顶上空的爱情》《麦子熟了》《月光粉碎》《遍地槐花》都渐次走向人心、人情、人性的审美,《下一站不下》则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完形”式的艺术建构。
首先,以“史”写“情”,人物的情感体验、灵魂纠结成为叙事的核心。小说主人公宋怀良命运故事的开始时间标定为1992年,那时他是国营庐阳无线电二厂的一个小电工。1992年这个时间点的设定,对文本中人物的命运以及文本自身的叙述而言都意义非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间”“新纪元”,也是一个“物质神话”即将降临的时刻。正是这个年份,中国正式拉开了市场经济的帷幕,姓“资”姓“社”的争论被历史终结了。小说人物的故事时间从1992年延续到2018年,时间跨度大约26年,也是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一个时代物质极速膨胀的历史阶段。小说客观呈现了宋怀良所经历的国营工厂的倒闭、失去女友汪晓娅、五里井街坊凑钱为父亲治病和发丧、被怀疑偷钱和兄弟陈琦的反目,与吴佩琳“谎言抑或神话”而既成事实的婚姻,以及后来抓住机遇成立装修公司,成为具有多个分公司的宋总。宋怀良的个人“发迹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史、一个时代的物质史几乎同步,来得太快竟然觉得不够真实,似乎就是“谎言或神话”。与既往的道德救世书写不同,《下一站不下》并没有将叙述重心放在创富神话背后的道德批判上,而是将主要笔墨聚焦于宋怀良的情感体验、灵魂纠结,也是许春樵试图展现一个时代物质史背后“人”的情感史、精神史和心灵史。小说叙述援“史”入“情”,而不是以“情”证“史”。这里的“史”就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一个时代的工业史、商业史和物质史。小说写出了这个时代物本主义对人本主义的挤压,尤其是欲望化时代扭曲的价值观对人性、人情、人心的全面侵蚀与重度异化。国营无线电二厂厂长的女儿吴佩琳当初放弃了大学学业,执意要嫁给穷困潦倒的小电工宋怀良,是因为看中了宋怀良诚实、善良、本分的品格。宋怀良为了回报吴佩琳的爱,拼命地想给吴佩琳体面的物质条件。他们创业之初,小两口相濡以沫,感情深笃。后来他们创办庐阳城的第一家装修公司,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他们之间的感情逐渐有了裂痕。裂痕随后修复,修复后又再度撕裂,直至最终发展到要离婚的地步。小说以宋怀良和吴佩琳情感体验中的甜蜜、纠结、矛盾以及痛苦为主要内容,以充分的故事、细节、场景、心理,极为传神地演绎了物质神话时代“人”的情感体验和心灵生活。小说的题目也一改既往道德对抗意味很强的命名,如“放下武器”“男人立正”“缴枪不杀”,也一改具有象征、隐喻意味的命名如“酒楼”“屋顶上空的爱情”,而是采用了较为形象化诗意化的命名“下一站不下”。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作家的“文本意图”已经不是创建二元对立的道德框架,以艺术的方式完成对物质时代道德失范的批判,而是在物质化欲望化的语境中,探讨世道人心的变异,以艺术的摹写建构人的情感伦理和心灵镜像,从一个时代的精神“内部”揭示特定时代的生存真相或从心理的真实抵达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处。
其次,文本对人物生命感受、心理征候的同情性理解超越了既往的道德判断。“两个好人在一起为什么过不上好日子?小说里没有对与错的简单裁决,只有人生浩荡的生命暗示。”小说封底这段作家的自我阐释,很明确地表明了,在宋怀良和吴佩琳的婚恋纠结中,作家没有采用道德裁决的姿态,而是真实“还原”了两性之间的生活、情感、心理的复杂性悖论性。文本不仅以主线索极为充分地演绎了宋怀良和吴佩琳之间的感情波澜,还嵌入了另外三段感情。一是宋怀良和前女友汪晓娅。当初国营无线电二厂待业青年汪晓娅之所以看上卑微、一穷二白的宋怀良,据说是宋长得像她的前男友,只是好景不长,在下海的浪潮中,具有艺术气质、曼妙身材和小资情调的汪晓娅便弃宋怀良南下海南了。命运总是充满了吊诡,若干年之后,宋怀良成了宋总,而汪晓娅因走投无路回到庐阳城成了高档会所的妓女。在会所的包间里,宋怀良和汪晓娅不期而遇,后来在宋的资助下,汪晓娅开了一家化妆品店,告别了自己的皮肉生涯。宋对前女友的资助引发了家庭矛盾。细究宋资助汪晓娅的心理,可能有多重:故人相见,两人身份境遇前后反差太大,是同情?是旧情?证明自己现在的成功?抑或男人的虚荣心理?无论出于什么正当或隐秘的心理,吴佩琳都有充分理由对宋怀良的行为和心理产生怀疑。二是宋怀良和公司财务总监张月秀的情感关系。张月秀是吴佩琳的闺密、要好的姐妹,当初是吴佩琳坚持要张月秀到公司任职并暗地里关注、监督宋怀良的日常行为。在公司工作期间,张月秀对宋怀良的为人处世渐生好感,恰在这时张月秀也和自己的丈夫魏国宝离婚了。宋怀良也对张月秀有很多理解和照顾,这个时候宋怀良和妻子吴佩琳因为汪晓娅的关系紧张,而且因为宋怀良和张月秀到外地单独出差的事解释不清,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多了一层意味或心照不宣。宋怀良和张月秀在肉体上没有出轨,但精神上是否出轨,小说叙事很是暧昧,这种关系就是当事人宋怀良和张月秀自己也是懵懵懂懂的。三是宋怀良和公司新来的设计师艾叶的感情关系。刚进公司的那会儿,艾叶身上的青春“另类”气质和浑不懔的做派,使得宋怀良对她没有好感。但她的设计艺术才华及后来表现出的单纯、热情、爽直的个性渐渐在宋怀良心里驻扎下来。这个时候他和吴佩琳正在离婚的冷战期,艾叶的出现确曾让宋怀良动心,甚至有一次在喝酒之后差点在肉体上出轨。好在宋怀良守住了道德底线,坚持要在离婚后给艾叶新的生活。此后吴佩琳突发肝病,生命垂危,宋怀良打算以自己的肝脏给妻子移植,这个时候公司也破产了,宋和吴的离婚也就彻底搁置。《下一站不下》在塑造宋怀良这个人物形象尤其是刻画其内在心理的时候,并没有采用道德化的眼光,带着放大镜去审视人物幽昧复杂的心理,对人性的多面性也没有进行纯化处理,没有将宋怀良塑造成道德上的圣人或纯而又纯的“君子”,而是真实地洞察其在欲望化的环境中心理的原生状态。对生命感受、体验的思考大于道德的批判或认同,小说因此拒绝了道德先验的主题,全面走向对人性的省察、审美,还原了生活、情感、心理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历史生成性。究其实,这部小说从整体上颠覆了既往的道德本质主义书写:“1990年代有一个良性的学术发展脉络,这个脉络就是反本质主义,或者说力图建构一种相对主义,当然今天也许要重新反思某种过度相对主义的诉求,但20世纪90年代的确是一个解构本质主义的时代。”吴晓东教授这里主要指的是学术,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大抵亦是如此。许春樵的这部长篇小说,也确实超越了既往道德本质主义叙述的路径,将道德、人性放置到20世纪90年代的具体语境中去考察道德、人性的具体处境,这种将道德、人性语境化、情境化、心理化的叙述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模糊色彩,从而形成了对道德本质主义叙述和人性窄化书写某种程度的偏离甚至解构。
再次,创作主体关于责任伦理、知识分子精神伦理与存在伦理,道德伦理与“发展”伦理关系的历史主义思考。“存在即合理”,这是欲望升腾时代的“发展”伦理和存在伦理。以“发展”的名义,可以不惜牺牲一切道德、良知、道义以及社会规则。“不择手段”“寡廉鲜耻”“逼良为娼”“分享艰难”……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知识分子退回书斋,犬儒主义广为流行,人的灵魂无家可归。作家许春樵多次、反复、深度聚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作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既往的道德化写作,作家秉持的是责任伦理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伦理,正如巴尔加斯·略萨于1994年在《致中国读者》中所言:“一个作家不能仅仅限于艺术创作之中,他在道义上有责任关心周围的环境,有责任关心他所处的时代,有责任关心社会上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由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情境出发,许春樵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悲欢、一贯的人民性写作立场,前期创作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姿态和正在行进的历史阶段相因相契,有其历史合理性、正当性、必要性和合目的性。这也是一个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责任伦理和精神伦理,是其自身“知识分子性”的适时体现。因此,他前期道德理想主义的救世“妄想”在欲望化时代看似荒诞、不切实际,却必不可少。无论被视为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还是被目为推石上山反抗荒诞的西绪福斯,这种富有勇气的反抗精神是物质化时代的清醒剂。当然,随着市场化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再一味地坚执道德理想主义和“清洁的精神”势必不合时宜,文学写作也要从与欲望现实的道德对抗高地上下撤,撤到更为宽广的世俗生活地带和人性、情感地带。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写作中道德标准的降低或者说不再秉持道德伦理、责任伦理和精神伦理,去认同发展伦理、市场伦理和现实存在伦理的合理性,而是以一种历史主义、发展主义的眼光重新照亮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并试图在这种多重悖论的时代和历史情境中展现个体的人的生存真相与精神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下一站不下》将叙事重点完全转向了历史或时代中个体的命运与情感。这有效地避免了吴义勤所批判的叙事模式:“历史/时代与人的关系是文学作品惯常的母题,历史/时代的不可抗拒性以及人与历史/时代命运的同步性是大多数作品处理这一母题时的基本模式。对历史/时代主体性及其对人的命运支配性的强调常常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给人一种‘历史/时代’大于‘个人’的感受,‘历史/时代’成为文学的主角,而‘人’反而成了配角。”这部小说成功地将“人”的命运、情感、心灵作为叙事聚焦的核心,而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变迁只是成了情感、命运、心灵“在场”的背景、场域或亲历者的见证。源于作家对责任伦理与市场伦理、知识分子精神伦理与存在伦理,道德伦理与“发展”伦理关系的历史主义再认知和辩证思考,小说摒弃了既往二元对立的道德思维框架,将故事和人物的命运放置到更为真实的历史情境中,从而获得了更为宽广和深厚的叙事空间。
三、叙述的调性与悲剧精神的贯注
(一)“我”的介入与文本的叙述调性。许春樵小说一贯具有反讽、幽默、调侃、嘲弄和擅长比喻、拟人修辞等叙述风貌或调性。李建军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基本调性,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特殊调性,甚至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总体调性……在评价叙事性作品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准确感受、把握、描述它的调性。因为,它是作品最重要的气质和风貌的集中体现,是一部作品的具有灵魂性的东西,是作品的情绪和格调意义上的主题。”《下一站不下》一方面延续了既往类似的叙述调性,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叙事格调。许春樵特别喜欢“我”对叙事的介入,从而构成文本意义上热奈特所言的分层叙事。《放下武器》中“我”是小说主人公郑天良的外甥,干过农药厂工人、保安兼打手、推销员,后来为了活命成了自由撰稿人,专门写各种类型的黑幕。尽管“我”和美容院的小姐张秋影关系暧昧不清,但并不妨碍“我”对事实真相的判断。《天灾》中“我”在三年困难时期,以“我”为视点见证了父亲许二贵身上发生的故事、特殊时期留给母亲的心灵创伤以及村民们政治化的生存情状。《生活不可告人》中,“我”也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正在为小说《月光下的单人床》寻找销路,在和书商洽谈的途中,接到二叔许克己出事的消息,开始了二叔故事的讲述。《下一站不下》中的“我”则是一名市文化局的剧作家,算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衣食之虞,可也背负着房贷的巨大压力。市文化局的局长找“我”写宋怀良,是为了获奖,恒达地产的孙总找“我”写宋怀良的电视剧,是为了宣传企业和商界精英。在这些叙事文本中,“我”的故事是第一层,然后由“我”的故事牵引出第二层故事:郑天良的故事、许二贵的故事、许克己的故事和宋怀良的故事。第二层故事是小说的主要故事层。有意味的是“我”的故事和主要故事层的故事构成一种特别的张力:《放下武器》中的“我”为生计所迫,舅舅贪腐的人生素材原本可以为“我”提供官场黑幕捞取金钱,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的良知发现,背离了写作的初衷;《天灾》中的“我”那个时期还未成年,以未成年孩子的视角状写生产队困难时期的政治和成年人的命运;《生活不可告人》中的“我”写的是情色一类的读物招徕读者,这个和二叔(克己)的人生道德原则存在龃龉和不可调和的冲突;《下一站不下》中的“我”也期待写出一部“江淮好人”宋怀良的剧本,从而获得翻身的机会,但随着访谈的深入,宋怀良的形象也是和孙总的诉求完全相左。这些文本“故事层”和“超故事层”彼此嵌套,戏中有戏,不仅让叙事摇曳多姿,也在张力结构、命运交织中体现出复杂的意味,正如青年评论家彭正生所言:“套盒结构作为一种叙事的物理形态,它本身并不具备价值(意图)创造功能;然而,伴随套盒结构而生的复调叙事却往往赋予小说多种‘声音’,让多种价值(意图)彼此对话。”文本中“我”的介入叙述所形成的类似复调叙事之间的审美间距,以及“我”和基本故事之间的龃龉,形成了特有的叙事调性。在“我”看来,许春樵的叙事调性有他的一贯性,即反讽、调侃、戏谑、幽默和风趣,这在《下一站不下》中仍多有体现。比如,小说中写“我”准备写宋怀良的时候,文本这样叙述:“孙总和局长对宋怀良的角色定位,都不是我想写的,但相较而言,我愿意为120万委屈自己,这就像走投无路时,在上吊和喝老鼠药之间选择,我选择上吊。”不过,这仅仅是文本表层的叙事调性,而在文本深层,《放下武器》时期的道德激昂、义愤少了很多,《男人立正》时期的沉重压抑的苦难叙述也淡化了,《酒楼》时期对传统文化断裂的焦虑、悲愤在叙述中也难觅踪影,《屋顶上空的爱情》中的忧伤、无奈似乎也疏远了。从总体上来看,《下一站不下》的叙事调性变得更加平缓、悲凉和低沉,小说以近乎旁观、冷漠的叙事语调,讲述发生在历史/时代宏阔背景下的凡俗人生、情感纠葛与命运悲欢。
(二)孤独、悲剧意识与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下一站不下》发现了个体灵魂深处的“孤独”,通过宋怀良和吴佩琳之间感情、追求、观念不相通的悲哀的体味和思索,揭示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孤独”的在世处境,同时也揭示了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哀与无奈。作家许春樵是一个灵魂的探险者,他潜入人物的心灵深处甚至是潜意识无意识的褶皱里试图探寻他们情感、人性的幽昧与复杂:“这两个生命真的‘同声同气’吗?他终于发现,在静默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当初,下岗工人宋怀良几乎深陷绝境,这个时候吴佩琳的到来,无论身心都给了他决定性的支撑。庐阳五里井破旧的陋室住着两个相濡以沫互相搀扶的灵魂。吴佩琳为了这份爱情和父亲决裂,拒绝了魏国宝、郭凯等的纠缠,放弃了大学学业……但她彼时心灵是快乐的。随着历史机遇和人生奋斗的叠合,他们的事业从卑微处起身直至一度如日中天,他们的情感却无法挽回地产生了龃龉和裂痕。吴佩琳追求的是家庭幸福、丈夫的可靠和事业的稳定,这也是当初她之所以“下嫁”给宋怀良的原因。而宋怀良对吴佩琳心怀感恩,其感恩意识、回报意识、向街坊邻居自我证明的意识、作为一个男人的事业野心以及对街坊邻居亲戚来者不拒的办公司的态度,都逐渐偏离了吴佩琳的“初心”。随着他们物质生活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抬升,他们情感的罅隙却在不断地扩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歧就是他们关于宋怀良的亲戚耿双河嫖娼的态度。吴佩琳坚持要开除耿,公司要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宋怀良则以当下装修事务繁忙为名,让其留下。吴佩琳的担心不无道理,随着公司业绩的扩大,为了揽工程,宋怀良也经常陪一些重要客户到“红蜻蜓”等娱乐场所为客户嫖娼包小姐埋单,尽管他只是陪同,并未实质性参与,但他这种包揽工程的做法已经等同于认可了社会的“潜规则”,以自己公司的“发展”伦理僭越了社会的道德伦理和婚恋的情爱伦理。他的言行和吴佩琳的追求是偏离的甚至相悖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感情的沦落也源于他们自身个体存在的“孤独”,尤其是心灵的孤独,源于他们无法真正实现心灵的契合。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家的悲剧意识、文本的悲剧精神以及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是创作的“前定”,叙事的过程就是展示从憋屈、心酸的生活走向崛起、风光的顶峰,然后从顶峰坠落,感情、心灵和人性上则是从相濡以沫到矛盾龃龉再到势同水火再到最后的悲剧性收场。整个的文本叙述让“悲剧性”“悲剧精神”“悲剧意识”得以充分、细腻、令人信服地展开。曹文轩说:“悲剧精神的觉醒,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觉醒,也是中国历史的觉醒。”从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到“男人系列四部曲”,再到最近这几年的《麦子熟了》《月光粉碎》,再到《下一站不下》,从许春樵整个创作历程看,作家基本上将“悲剧意识”“悲剧精神”贯彻其创作的始终,这也是一个作家清醒的创作意识,因为“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就是在一些较高的社会学层面或哲学层面上来表现人的永无止境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悲剧性快感”。从这一视角而言,我们获取的并非视角主义的片面,而是一个作家对这个特定时代的文学良知、思想坚守和深刻的社会认知。悲剧创作的伦理不是为了展示苦难、渲染伤痛和命运的悲剧性,也不是要博得别人的同情和怜悯,而是要从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上获得直面“悲剧”的现实精神,获得超越悲剧的超越精神,获得与悲剧命运抗衡的崇高感与反抗精神。由小说人物宋怀良的悲剧命运,自然延伸至他内心的忏悔意识。小说邻近结尾的时候,宋怀良的公司彻底破产,艾叶嫁给了外国人,妻子吴佩琳身患癌症(后被证明是误诊),需要肝脏移植,而没有合适的肝脏来源,他自己去做了各项身体检查,医院说他的肝脏不适合其妻子的器官移植。这个时候的宋怀良走投无路,内心充满了绝望,他留下了遗书给吴佩琳,选择了到摩天轮上自杀。他的生命没有终结于自杀,而是阻止小偷偷窃而终结于被小偷的捅伤。他因此成了见义勇为的“江淮好人”。这封给妻子的遗书文本中并没有给出具体内容,读者可以不难想见,这是一封宋怀良给妻子的忏悔书,忏悔自己违背了情感的初衷,导致了家庭、公司、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忏悔自己虽没有肉体上的出轨,但也确实存在着精神上的出逃和情感上的游离。忏悔自己深爱着妻子,而自己的心理和言行却背离了爱情起始的坐标和方向,忏悔自己无能,无法为妻子挽回生命,甚至于妻子治疗的费用还要到处变卖物产或筹集……所有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无可挽回,唯有忏悔和以死赎罪。
(三)故事性、戏剧性及其之上的叙事追求。许春樵的小说历来好看,即使是一些貌似先锋的文本,也在先锋叙述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故事。《下一站不下》可以解读为个人情感的故事、创业的故事、成长的故事、忏悔的故事、命运的故事,同时也是时代/历史的故事。尽管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1936)一文中宣称,讲故事的艺术已经是日薄西山,尽管我们发现从远古神话、史传人物、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的笔记体小说,讲故事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故事之于小说、之于叙事,至今并未走向没落,莫言还在宣称自己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千零一夜》以无穷尽的故事叙述了人的命运:“叙事等于生命,没有叙事便是死亡。”因此,对故事的讲述依然是当下小说叙事的重要依凭,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正是由于早已存在着的人际关系之网(它有数不清的相互冲突的愿望和意图),使得行动几乎达不到它的目的。但也正是由于这一中介物(在这当中,只有行动是真实的),才使得行动如同制造有形物品那样自然而然地、有意或无意地‘生产’出许多故事。”许春樵在经历先锋历练之后,又回到了讲故事的现实主义叙述,这和其他先锋作家如余华、格非、苏童如出一辙,这并不意味着叙事立场的后撤,而是如卢卡契一样自觉意识到:“对故事的维护,并不是对一种所谓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的重视,而是他把叙事看成一种具有社会伦理功能的艺术形式,文学写作也许并不是适应现实的一种妥协手段,而是一种抵抗形式或批判形式。”《下一站不下》每节的小标题都带有“故事性”,从第一节“诱惑之外,倒闭的工厂与爱情”至第二十二节(最后一节)“下一站不下”,人物的命运就在这些故事和情节中一步步走向读者。深邃的思想意蕴与故事性的叙事外貌两者水乳交融,妙合无垠。当然,故事的好看、耐看依赖戏剧性的情节设计,许春樵并不反对情节的戏剧性,这部长篇小说又一次“故技重施”,在很多地方营构了戏剧性的场景、冲突、事件,这些戏剧性的叙事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故事的讲述,也承载着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同时也对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心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陈琦的3万元被盗事件,宋怀良和吴佩琳卖墓地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在红蜻蜓娱乐会所包厢宋怀良和汪晓娅的不期而遇,宋怀良被小偷刺伤事件,等等。小说具有明显的故事性、戏剧性,在此基础上,许春樵对叙事品质和叙述语言有着非常高的追求,同时他还受影视剧叙事的启发,写人物、写生活是“贴着地面写”,在写作中充分感受小说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也是一种情感沉浸式的写作。
四、结语:“后道德理想主义”书写的可能性向度
道德理想主义是既往贴在许春樵身上的创作标签,从《麦子熟了》伊始,到《下一站不下》的“完形”,许春樵突破了道德理想主义写作的瓶颈,走向了人性、心理、情感、生活等更为广阔的审美场域。这里并非指认前期道德理想主义的书写是一种不好的创作,相反,这种创作应时而生,与20世纪90年代欲望化的世俗生活构成对话、交融、镜像或拯救的关系,是有痛感、有温度、有力度、有热度的写作。从不同的层面对人物形象和社会生活做出善与恶的或超善恶的价值判定,在善恶意义上的道德感动或义愤与20世纪90年代普遍的世道人心相结合,从而抵达了深刻广博的道德境界。时代语境的变化,必然呼唤作家创作的改变,当道德理想主义书写的资源、历史合理性消耗殆尽的时候,创作的转型势在必行。对长期致力于“道德理想”与“精神立正”创作的许春樵而言,创作主体面临的必然是其“后道德理想主义”的写作如何成为可能。这也符合朱寿桐所分析的道德和文学创作之间的逻辑进路:“从‘蓄道德,能文章’的传统出发,经由将人生道德与文学宣扬的道德相统一的古典时期和民间形态,到一般的人生道德与文学渲染的道德的分离,再到文学超越于一般善恶,在更高的人类困境、弱点和疾患等方面审视通常纳入道德批判的种种罪恶和荒诞,这是文学历史发展的一条清晰的线索。”所以,“后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学书写,一方面可以超越既往的道德善恶的价值判定,从人类的困境、弱点和疾患中重新审视人世间的罪恶和荒诞,如《下一站不下》,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泾渭分明的道德判定,而是潜入人性的深处去审视人的道德处境和心灵幽昧,这就会导向对小说中人的境遇的同情、悲悯,导向道德书写的人性维度,关注人物宋怀良和吴佩琳以及其他人物在特定时代环境中(20世纪90年代)的人性体验和生命状态,也就是探寻在“宏观历史”中的“微观人性”,表现在历史进程中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示一个物质时代背后人的精神史、心灵史和情感史,而不仅仅是对特定时代的道德评价。另一方面,就是在文学创作中重建“生活总体性”。这里的生活总体性就是在时代/历史/现实的框架下,在自然、生存、压抑、反抗、进化、本能、情感、意志、风俗、伦理、文化等多重维度下,形成人性的聚合体,聚焦人的生存景观和心灵图谱。如此,“后道德理想主义”的书写,就能走向人性审美的浩阔,以“历史的、审美的、人性的”(丁帆语)标尺营构一个更为博大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