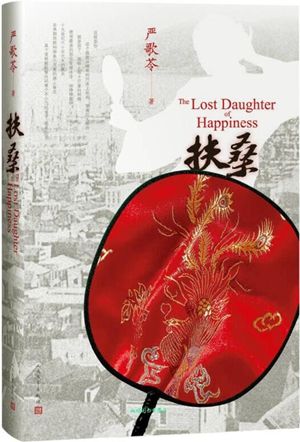
《扶桑》,严歌苓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扶桑》于1995年由著名美国华人作家严歌苓创作,同年,该小说获“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02年,登上美国《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小说榜,名噪一时。《扶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晚清时期(19世纪60年代),中国女人扶桑在广东被卖猪仔,来到美国旧金山寻夫,因为没有经济收入,只得从事妓女行业,在这过程中,与唐人街领袖大勇和白人少年克里斯之间的情感纠葛。她曾和克里斯产生爱情,最终虽未和他在一起,但却救赎了克里斯。故事结尾,扶桑发现大勇才是她在中国的未婚夫。在大勇即将被白人处死之际,双方在刑场上举办了婚礼,扶桑捧着大勇的骨灰回到祖国。假若是从东方文化的立场上讲,只要是存在强调欧洲优越性的陈词滥调,存在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并以此为方法进行文学形象建构和叙事链条拼接的,都只能是一种非真实的扭曲作品,而对于西方人来说,文学艺术作品追求、达到“东方人被西方人征服、拯救”的叙事语境框架,恰恰是他们的理想,二者形成了矛盾。《扶桑》恰恰就是这样一部实现了突破、化解此类矛盾和窘境的好作品。
《扶桑》是如何化解这类窘境的?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巧妙使用了双重叙述视角。一方面是“东方化”,严歌苓将一半的笔力放置在描写妓女扶桑上。她将扶桑放在19世纪华人到美国寻梦的大潮流之中,在展现名妓在寻梦的道路上面临种种艰难时所表现出的既堕落又包容隐忍的双重文化性格的过程中,作者使用了四种叙述视角(“我”、克里斯、大勇和其他的人)进行叙述,既全面又深入。每个视角都代表着一种视角和文化语境,让读者看后觉得合理又新奇。每个视角的文笔描写也极为细致、独到。除此之外,作者再通过描写扶桑与其他人物的爱恨情仇,着力渲染东方(中国)文化的神秘、玄奥、原始、非现代性和落后性,以期说明东方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浪潮之下,逐渐被表述和建构为“依赖性、毫无优秀性”的次等文明的“东方化”过程。
另一方面是“反东方化”,严歌苓将另一半笔力用来塑造与扶桑性别相异的两大角色——唐人街飞镖帝大勇和骑士先锋克里斯。其中,大勇是被建构起来的突破东方学视角的中国雄性角色,同样是被建构的角色,最终被东方气息所救赎的克里斯则是作者用来表达其大同儒家理想的重要人物。
由于这两个“一半”配合得非常默契,因此,无论是对于西方读者,还是对于东方读者来说,《扶桑》均成为一种超脱于读者既有文化语境、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的完美体验,特别是大勇和克里斯这两个人物言语、性格、品质、处事方式、人生观、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让人感觉到全新的美感体验和精神震撼。中国著名电影导演黄建中就曾对严歌苓说,“《扶桑》是我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从没想到人可以从那样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所以我觉得它那么好看,觉得耳目一新。”
一、扶桑:包容、堕落的双重文化性格
扶桑花又称朱瑾,在我国岭南一带是常见的观赏性常绿灌木。屈原有诗“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就有扶桑树了。西晋时期,有《南方草木状》对扶桑花进行记载。同时,它不仅仅是一棵树,它又是中国神话当中的灵地之一。传说扶桑就在极东大海上,太阳女神羲和大神和她的儿子金乌从扶桑驾车升起。可以说,扶桑历经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逐渐内化整个中华族群的集体认同,成为中国南方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并不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那样标志性,但也从另外一方面,即表达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柔美、柔弱、不争、平易的特质上有一定代表性。严歌苓以扶桑命名女主人公,意味着扶桑所代表的文化含义也同时内化为女主人公的精神品质和文化品质,这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特质同时内化为扶桑的特质。她在小说中这样描写扶桑的外貌,从外及里的手法让读者很快就能捕捉到扶桑的气质,进而了解到扶桑背后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家和佛家的精神风貌:
“嫌短嫌宽的脸型只会给人看成东方情调。每一个缺陷在那时代的猎奇者眼里都是一个特色。”
“脸上无半点担忧和惊恐,那么真心地微笑,是自己跟自己笑。一对大黑眼镜如同瞎子一样透着超脱和公正,那种任人宰割的温柔使她的微笑带着一丝蠢”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曾这样评价《扶桑》中的扶桑的笑,“而周旋在中、美寻芳客,及中、美丈夫/情人间,扶桑肉身布施,却始终带着一抹迷样的微笑。这笑是包容,还是堕落?”“堕落”和“包容”二词可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道家和佛家当中某一方面的特质,也可以用来概括扶桑的性格。“堕落”是贬义词,“包容”是褒义词,二者就是阴阳调和、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包容中包含着堕落的成分。没有底线的包容,就是自暴自弃。另一方面,堕落有时候是包容最后的归宿和结局。堕落本身就带有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抛弃,对传统道德伦理之外无节制的无底线的包容,有时候就等同于堕落。扶桑这一文学形象的塑造就是为了让身处不同文化立场的读者在包容和堕落、贬义与褒义的双重感觉与判断中,去设身处地理解另一种文化立场的合理性。同样的一个读者,他被“要求”既能从西方角度上理解这一妓女形象的妖娆、艳丽和神秘。从另一方面讲,也能从东方角度上理解她在面对生存危机时,所采取的处事哲学,以及所受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世俗化的、民间化的儒家理念)的强烈熏陶。
文中多次谈到,留着长辫的中国男子与白人男性即将发生冲突时,中国男子往往保持沉默或嬉皮笑脸,避免发生纷争,而这却更加激怒了一向爱好竞争和争斗的白人男性,最后中国男子或被毒打,或直接被缢死。扶桑何尝不是这样子委曲求全,妥协于强者之中呢?她戴着众多白人嫖客赠送的戒指,却不愿意和任何一个白人发生爱情。她心甘情愿地被绑架,不做任何的反抗,并差点与他人成亲。她被“拯救会”拯救出来后,本来已经有独立生存的可能性,却很快承认“自己是贼”而向大勇投怀送抱。最终,她表面上选择了大勇,却还是和其它嫖客日夜交合。总之,她看似不断地委曲求全,逃离弱者走向潜在的强者,却又总是“反者道之动”,不断走向事情的另外一面。
“你的沉默,和你心甘情愿的笑使识货的人意识到你绝不是一般的货色。”
最后,扶桑还是选择和大勇结婚。即便她不喜欢大勇,但这种结婚方式可以使得她不再受到所谓爱情的纠结(因为大勇已死,无法再干涉她。她也可以借口已婚说服自己不再相信爱情)。她的灵和肉一直在分开,在任何苦难面前都可以从容,是因为她相信“齐物”“混沌”,所以根本就不在意,也很容易去宽恕别人。但是,在唐人街暴乱中,她却第一次在被凌辱被性暴力中感觉到屈辱感,这是因为她爱上了克里斯。最终她原谅了克里斯对她的凌辱,从此她不再受到爱情的折磨,也彻底自由。综上,扶桑的遭遇看起来非常奇妙,她的很多选择暗喻了东方文明在面对源头迥异的强势文化时所采取的在夹缝中生存,明哲保身的态度。由于《扶桑》介绍的是美国旧金山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它反映的也是首次在西方土地上上演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正面交锋、正面冲突,所以,扶桑的处世态度、做事原则,以及身上所体现的纯粹的道家式的品格和雌性气质,也成为了华文文学描写此类文化冲突、性别压迫、种族歧视等的滥觞和标杆。
二、大勇:被建构的“反东方化”的雄性角色
萨义德曾在《东方学》中,将对种族的刻板偏见与文学想象的设计和塑造之间的巧妙关系概括成,“伦理概括的力量为一种刻板的思维所加强,这种刻板的思维将戏剧性乃至原型性的人物——原始人、巨人、英雄——作为当代伦理、哲学甚至语言问题的来源。”因此,西方人对于东方人“原始”状态的认同便衍生出系列的文学作品和系列的文学形象。长期以来,(东方)中国男性的男性气概长期被白人男性霸权气概所否认和压制,从而在主流文化中形成了懦弱无能、狡诈、阴柔顺从的刻板印象(例如臭名昭著的傅满洲形象)。
《扶桑》中出现的华人男性形象,也多为这种刻板印象,例如上一节提到的被殴打和被吊在树上惨死的华人男人,以及让白人们既想一探究竟又想保持距离的男性戏子。这些华人男子形象都真切地贴合了西方主流文化对东方男性缺乏男子气概,阴柔化、女性化的偏见。
然而,严歌苓笔下粗犷野性的大勇是一抹冲破阴郁云层的阳光。这一角色男性化意图极其明显,它改写了西方主流文学为黄种男性树立的不可动摇的刻板印象。和细致描写扶桑的气质一样,作者也详尽描写了大勇的外貌和旗帜。辫子在以往是华人男子形象的象征,可大勇的辫子不像其他“被阉割”的男子一样细细短短,而是又粗又长,散批开来,就像是马鬃或者狮鬃,有一种兽性的美。在阳刚的外表下,大勇是一个具有反抗种族压迫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他不仅以暴制暴,而且还善于进行东西文化权力话语的对峙和反抗。福柯曾这样解释权力话语,他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权力所到之处,就有服从和反抗的双重力量。在《东方学》中,将这一关系的阐述为东西方(文化乃至所有的一切)之间的互动关系。说到底,萨义德想表明,当今世界的权力话语流动,就是西方对东方的压制和东方对于西方的文化反抗。《扶桑》之中,大勇就是这样一个向西方争夺权力话语权的东方人物。他集智慧和武力于一身。在武力上,他的飞镖神话让残暴的白人闻风丧胆。
“阿丁不光在唐人区有声名,洋人也对他的神鬼故事有传闻,说是那次四十个中国男人被剪了辫梢,第二天就有上百洋人的衣裳后背出现了刀口。那刀齐齐地戳透外衣、马夹、衬衫,并不伤皮肉,似乎是在直戳心脏的途中突然收了杀心。”
在智慧上,他成功引导华人民工们集体停工罢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成功使得中国苦力的罢工登上报刊,也使铁路股票开始回落,真正使得美国管理阶层和精英阶层开始重视这个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在他身上体现出许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品质,特别是“忠义”信念、“仁者爱人”的关爱意识、不畏生死的生死观和惩奸除恶的侠义心肠。除此之外,他也受优秀儒家家庭观的熏陶,有强烈的家庭观念和乡土情怀。他虽然在处理外界事务时展现出很强的手腕,甚至有藐视美国法律的勇气和凶狠残暴、精明狡诈的手段,但他唯一的软肋就是他深爱的妻子,“从不见面的妻子”,当有一天“一个蹲在市场上刮鱼鳞的穷苦贤惠的渔妇冲他抬起黄脸,手在围裙上匆忙涂抹,掏出一封揉得掉渣的信”时,他“心里出现了一股酸胀”,后来竟想杀掉他一直爱怜但未达成婚姻契约的扶桑。
除了展现出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熏陶的武力和智慧之美之外,他在物质条件上也极为丰盛。他也可以像英美绅士一样穿着典雅华丽,风流倜傥,举止端庄。“于是唐人区就有了个逍遥的阿丁,穿最名贵的绸缎,戴英国人的帽子,手里提一个装首饰的皮夹子。夹子里是他的日常首饰,供他不断替换。兴致高的时候,他一天会换三次不同的怀表。他的首饰匣子也是他的钱包……”
《扶桑》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碎片化描写,在这里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大勇集以上众多优秀品格品质和物质条件于一身,作者认为,这些都来源于他在精神、人格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良好继承。作者通过大勇这一真实的,有男子气概的形象塑造,消解了西方文学对于华人缺乏男子气概、缺乏斗争精神,软弱无能的刻板印象,超越了西方人对东方男子、东方文化体系的固有理解程度,打开了西方重新理解、认识东方的新角度、新局面。
三、克里斯:身处东方想象之下的大同思想实践者
在《扶桑》中,克里斯是一个停留在固有东方想象中,又表达出作者儒家大同思想救赎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的文学形象。通过克里斯,扶桑道出了作者对于未来东西方文明发展的看法和觉悟,这种觉悟类似于福楼拜未完成的作品《布瓦尔和白居谢》中所预见的:
“现代人在不断进步,欧洲会通过亚洲而获得新生。人类文明的历史规律是从东方转向西方……两种形式的人性终将融为一体。”
文化融合的世界观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认识到文化的非孤立性是促进文化融合的首要条件。回溯起东汉初期释佛宗教传入中土的时候,也一度在中国各个阶层中激荡起反对情绪,但随着时代的迁徙,融合的声音远远大于反对者。最终,佛教文化成为影响中国古典文化最重要的外来因素。返回到《扶桑》中,作为出生在军人世家的德国后裔克里斯一开始像很多人一样,被固有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想象所控制。第一次见到扶桑的时候,他就觉得扶桑丰润圆庾的肉体就像“浆汁越灌越满的果实”,他梦想去摘下这个果实自己享用,喜欢并愿意陷入这种东方式气质当中,但同时,他又畏惧扶桑的神秘、原始气质。他的童年和少年都被这种“又惊又怕”的心情所笼罩,脑子当中被扶桑的形象充斥而魂牵梦绕,幻想和对扶桑的不断寻找组成了他的生活。由此出发,在他心中激荡起了西方对东方的探索甚至殖民、统治或毁灭的冲动,以及居高临下、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传统骑士激情和热情。他为此在15岁时反叛家庭,反抗父亲监禁而成为“叛逆者”。离开原生家庭之后,他想完全拥有扶桑这个廉价优美,但又渴望又不可及的中国妓女,这种拥有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拥有,更是一种还其自由的成全与救赎。而比克里斯年纪大许多的,正如日中天的唐人街霸主大勇成为这一切的障碍。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克里斯内心燃烧,大勇取代父亲成为他的暗杀对象。但是,青涩的克里斯无论从经济条件上,还是从经验想法上,完全不是大勇的对手。内心强烈的挫败感和自尊心让克里斯时刻想要复仇,最终导致在他加入了白人对唐人街,以及对扶桑的暴行。至此,可以说,克里斯的经历、生活,所有的举动和反应均基于其对于东方的想象,而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东方想象,他的一生被扶桑所影响,为其后来融合、调和各种文化,成为反对文化霸权的斗士奠定了文化基因。
在参加暴行之后,克里斯开始对此忏悔,并试图用“他还没有成年,仍然年幼”的方法来安慰自己,虽然没有收到任何责罚,但内心的自我拷问往往是最折磨人的,也可能将是持续终生的。他离开了美国,17岁时回到故地,并开始有所行动,在“拯救会”开办的学校教中国学生英文。克里斯得到了扶桑的谅解,他感觉到满足,甚至开始在做更大的全人类的事业,即为中国文化着迷并奔走。他觉得这样子做会从心灵上更加得到慰藉,得到扶桑的肯定和认同,“被扶桑改变了的一生。他一生都在反对迫害华人,也反对华人间的相互残害。他成了个中国学者。他觉得扶桑在看他做这一切,不论他赞同还是反对,她总是在看着他的。”
在小说的结局,克里斯最终成为忠诚的“大同理想”的实践者和勇士。《扶桑》的叙事策略就优在它从两个方面实现了“反东方化”的建构。一方面,《扶桑》从大勇等形象的建构,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拥有强大力量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作者更有意通过克里斯这一白人形象,从西方人的角度出发,满足其原有的文化认知和炽热的东方想象。同时,严歌苓试图揭示,这种东方想象是虚构的,但也是自然而然的,无需恐惧,正如《东方主义》所说,
“世界如果没有了对东方的想象,那将是何等可怕。”
“东方主义是一种形式的内部反思,其所关注的是西方的智识关注、问题、恐惧以及欲望,而这些都降临到一个虚构的按照惯例被称为东方的对象身上。”
假如《扶桑》中缺乏克里斯的形象,《扶桑》将很难在西方读者中博得认同,并且很难成为一部真挚可信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