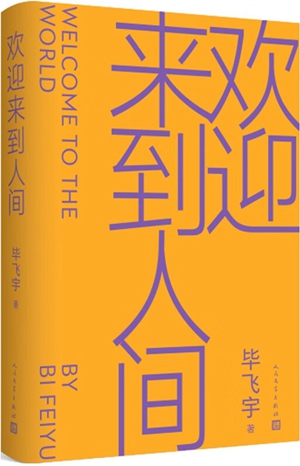
《欢迎来到人间》,毕飞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依照我多年来的阅读经验判断,毕飞宇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极有可能成为2023年度中国文坛的一部现象级作品。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一判断,一方面固然由于毕飞宇身为茅奖获得者,在读者中有着相当大的号召力,但另一方面,更是基于作品本身思想艺术品质的不同凡响。其中,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成熟征用。
小说是细节或者说局部的艺术,即使是篇幅相对浩大的长篇小说,也是由很多处成功的局部描写支撑起来的。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恰好就是一部有很多处迷人局部描写的长篇小说。先后两次认真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我的感觉如行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文本中那些迷人的局部描写,很多时候都会令我驻足不前,流连忘返,乃至玩味不止。
比如,小说一开头,作家所采用的,就是一种由大到小逐渐缩微的艺术聚焦方式。从一向被老百姓称为“市中心”的千里马广场落笔写起,再到户部大街(后被称为南商街)和米歇尔大道(后被称为东商街)这两条纵横交汇的城市大街,又进一步缩微到恰好位于南商街和东商街交叉点上的第一医院,并最终落脚到作为第一医院主楼的外科楼。然后,就是由外科楼而生发出来的关于中国人就医观念的一大段妙论:“人们拿吃药、打针和理疗不太当回事。即使患者死了,人们也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谁还能不死呢……出于对‘元气’的珍视和敬畏,中国人普遍认为,外科更复杂、更尖端、更艰难也更神秘。所以,看病有看病的易难程序:吃药、打针、手术刀,这就有点类似于女人的战争升级了:一哭、二闹、三上吊。”虽然从医学的层面上说,各个科室理当被平等看待,但如果考虑到中国人的习惯心理,更看重所谓的动手术,所以,外科的地位在实际情形中还是更重要一些。依循如此一种逻辑,如同泌尿外科这样的专门性的科室,自然也就比普通外科显得更重要一些。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的故事情节,便集中围绕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的主刀医生傅睿而充分展开。
再比如,王敏鹿和傅睿相亲时的场景描写。因为父亲傅博身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党委书记,所以傅睿在医科大学自然也就是传说中天花板式的人物。而同为医科大学生的王敏鹿,则出生于本埠城南一个极其普通的平民家庭。这样的两个家庭,要在一起相亲,一种不对等的尴尬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关键的问题是,毕飞宇到底怎样才能将如此一种尴尬的不对等情形表现出来。“王家是三个人,傅家也是三个。一样的空间,一样的桌椅。但是,傅家人是如此不同,有阵仗。阵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敏鹿也说不上来,它在,无形,兀自巍峨。傅家的比重大,权重更大。敏鹿知道了,她不是来相亲的,她面试来了。气氛在刹那间就压抑了。说压抑实际上也不对,‘那边’轻松得很,一点都没有仗势欺人的意思,相反,客气得很,谦和得很。”两家人聚到一起,虽然什么都没有说或者做,但来自傅家的看似无形实则四处弥漫的强大气场(也即阵仗)却已经形成。傅家人的表现越是客气、谦和,那种压抑感就越是明显。如此一种情形下,格外敏感的王敏鹿所生出的,无论如何也都只能是接受“面试”的感觉。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看似没有写情节或对话,但毕飞宇却硬是把两个不对等家庭相亲时的尴尬场景给写了出来。在王敏鹿原来的理解中,既然出身于阵仗强大的傅家,那傅睿自然也一样会强势无比。没想到,仅仅只是二人第一眼对视,内心里张皇失措的傅睿就已经败下阵来。某种程度上,正是傅睿意外的慌张,使王敏鹿于不经意间扳回了一局。从根本上说,正因为相亲的双方借助于傅睿的慌张而获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才最终成就了这一桩婚姻。既如此,毕飞宇小说中这一场相亲的场景描写,真正可谓深得心灵辩证法的精髓。
迷人的局部之外,就是结构设定的合理与丝丝相扣。整部《欢迎来到人间》,其实由三条结构线索组合编织而成。如果说傅睿的相关故事可以被看作是一条结构主线,那么,围绕老赵和小蔡这两位人物所发生的故事,就可以被看作辅助性的两条次要结构线索。倘若缺失了它们的存在与介入,以傅睿为中心的那一条结构主线的相关故事情节在一些关键时刻就会失去有效推进的动力。
但在具体展开关于傅睿的相关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关注的,却是被毕飞宇含蓄地表达出的某种社会批判要旨。此前,在谈论到现代主义和社会批判之间关系的时候,笔者曾经写下过这样的文字:“一提及文学深度介入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耳熟能详的文学术语,那就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如此一种联想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文学的批判性,似乎天然地就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这是一种明显不过的错觉。……通过现代主义或者说先锋派的一种写作方式,作家们也一样可以抵达深度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艺术意图。……只要将我们的视野扩大至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即不难发现,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而且也有着不容轻易忽视的批判性。也因此,倘若说批判现实主义已经是一种广有影响的说法,那么,同样也可以成立的说法,就应该是批判现代主义。所谓‘批判现代主义’,也即以一种现代主义的或者说先锋派的艺术方式来积极有效地实现一种深度介入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意图。”如果说所谓“批判现代主义”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毕飞宇的这部《欢迎来到人间》当仁不让。
与作品的社会批判意旨紧密相关的一个人物形象,首先是身为傅睿患者的老赵。老赵退休前曾经长期担任某一报社专门分管广告工作的副职,对于仕途上没有更多想法的他来说,这一职位已经足以令他心满意足。“无论老赵如何的不贪,架不住他的命好。就在老赵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巧遇了房地产的高歌行进。他赶上了。”因为老赵在报社分管广告,他才会在社会上结交与房地产紧密相关的一众朋友,养成了热衷于买房子的业余爱好(请一定注意“业余爱好”一词的辛辣讽刺意味):“每次只买一套,一滴;老赵还有一个业余爱好,他喜欢卖房子,每次还是一套,一滴。”老赵如此这般多年努力的结果,就是:“终于有那么一天,老赵的游戏换了一种打法,他把手里的房子一滴一滴地全卖了,换成了北京一滴、上海一滴、广州一滴、深圳一滴、青岛一滴、厦门一滴、成都一滴、三亚一滴。和什么都没有一个样儿。就在老赵快退休的时候,老赵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却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他冲出了亚洲,直接抵达了世界。旧金山一滴,洛杉矶一滴。这一切都不是老赵精打细算的结果,是水到渠成。”仅仅是一个看似闲云野鹤的报社分管广告业务的副职,自己都没有怎么耗费心思,竟然可以在全国各大城市,乃至于美国的旧金山和洛杉矶都拥有房产,在说明老赵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官的同时,更说明所谓腐败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性与制度性的腐败。一方面,把一个实实在在的贪官表述为“确实不贪”,带有鲜明不过的反讽意味;另一方面,把老赵带有一定被动性色彩的贪腐行为表述为“只能说,时代是宽阔与湍急的洪流,他没有被抛弃。仅此而已”,则再一次充分表明,如同老赵这样的腐败体现出了一种怎样的时代性色彩。关键还在于,与一般的反腐书写不同,毕飞宇看似轻描淡写,只是通过一连串“一滴一滴”,就举重若轻地洞穿了腐败这样一种沉重的社会现实。无独有偶的是,毕飞宇对于开发银行副行长郭鼎荣的贪腐描写,也处理得极富暗示性,真正可谓是匠心独运。明明是他的下属小裘姑娘要和他一起联手搞一次骗贷行为。“一亿三千万。依照三个点的返还率,小裘的这一票确实又不算小了。”如此巨大的一笔贪腐交易,作家却只用看似特别家常的对话写出。小裘说:“家里的事,你给个话。”郭鼎荣的回应竟然是一句问话:“家里都好吧?”小裘答:“好。爸挺好的,妈也好。你放心。”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孩子也好。”郭鼎荣说:“我还有点事,你先休息吧。”小裘瞥了郭鼎荣一眼:“好。你也别累着。”郭鼎荣的回应是:“知道了。”一场巨额资产的巧妙侵吞,就这样在如此一番不动声色貌似土匪黑话的过程中完成。借用现代作家李劼人两部作品的标题,就是看似“死水微澜”,实则“轩然大波”。
与类似于老赵和郭鼎荣这样的腐败相比较,更为严重,也更具有普遍性的,是一种带有突出专断色彩的怠惰性政治状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傅睿一次不期然的惊觉上。那一次,因为医院发生了医患纠纷,作为当事人的傅睿无论如何都必须出现在单位领导的谈话现场。正是在那一次的谈话现场,傅睿有了一种惊人的发现:“雷书记和自己的父亲实在是太像了。这个像并不是长相,而是说话的口吻,还有手势,还有表情。连遣词造句和说话的腔调都像。当然了,最像的要数这个了——他们的语言和他们脸上的表情往往不配套。这么说吧,在他们表达喜悦的时候,他们的面色相对严峻;反过来,到了‘教训很沉痛,很深刻’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却又轻松了。”明明既没有血缘关系,更没有在一个家庭里共同生活的经历,雷书记的举手投足为什么会和父亲如此相似呢?对于傅睿所不可能参透的内在奥秘,叙述者紧接着给出了相应的解说:“傅睿所不知道的是,眼前的雷书记和自己的父亲一直工作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父与子的相处。单位里的工作就这样,一个用心地教导,一个用心地模仿,耳在濡,目在染,上下级之间难免会越来越像。”一种无法被否认的事实是,尽管说父与子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可能会超过如同傅博和雷书记这样的上下级关系,但从根本上说,血缘关系终究还是敌不过现实生活的社会政治规制,所以类似于雷书记和傅博之间超越血缘关系的相似性现象的出现,自然也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傅睿在进入那个培训机构之后的发现:“中心主任则开始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自我检讨,然后,盛赞傅睿、讴歌傅睿。他的口吻和行腔和第一医院的雷书记很像,和傅睿的父亲很像。应该是传承有序的。因为是礼堂,中心主任的讴歌和第一医院的小会议室不同了,有了排山倒海的气势。这一次傅睿没觉得自己是烈士,他没能静悄悄地躺在万花丛中。讴歌是多么地残暴,傅睿是患者,被捆好了固定带,他已经被推上了手术台。灯火通明,无一阴影。这一台手术要切除的不是肾,是傅睿脸部的皮,也就是傅睿的脸。傅睿很清醒。傅睿知道了,麻醉师没有对他实施全麻,是局部麻醉。稍后,中心主任、雷书记、老傅,他们齐刷刷地站在傅睿身边。傅睿的父亲,老傅,终于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手术刀。他主刀。他要亲手剥了傅睿的脸皮。傅睿亲眼看着父亲手里的刀片把自己的额头切开了,中心主任和雷书记一人拽住了一只角,用力一拽,傅睿脸部的皮肤就被撕开了,是一个整张。傅睿的面目模糊了,鲜红的,像一只溃烂的樱桃。却一点都不疼,只是痒。”请原谅我在这里转引了如许之多的原作文字,倘不如此,就极有可能断章取义,难以把作家的写作意图完整地传达出来。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以上这一段充满超现实感觉意味的描写,乃是一种明显不过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类似于这种荒诞意味特别突出的超现实局部描写,在《欢迎来到人间》中并不少见。其次,如果说雷书记由于上下级关系而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受到过傅博的熏染,那中心主任跟傅博之间的关系却可以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如此一个陌生人,竟然也会跟傅博、雷书记他们形成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关键原因也只能到他们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忽视他们三个人社会身份的一致性:无论是已经卸任的医院原书记傅博,还是继任者雷书记,抑或培训中心的那位主任,他们的共同身份,都是单位的一号领导者,最终决策者。而潜隐于他们身后的,则毫无疑问是某种已经迁延日久形成了自身怠惰(或者说懒政,或者说专断,或者说在很多时候都会罔顾事实)的官僚机制。从根本上说,正因为他们均属于这一套机制所打造出来的产品,所以,原本看起来完全不搭界的他们,才会成为一个模子里打造出来的人,才会无以避免地形成共同的思维和精神特征。也因此,如果我们把此前那位“确实不贪”的贪官老赵和傅博、雷书记以及中心主任他们联系在一起,一个可信度极高的结论就是,毕飞宇对中国式官僚机制的某种弊端其实有着极其精准到位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在这个基础上,说《欢迎来到人间》是一部优秀的批判现代主义作品,当然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判断。在其中,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毫无疑问是犀利的社会批判与辛辣的政治讽喻。
不知道为什么,在先后两次认真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俄国作家布尔加科夫那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白痴》。虽然无法从毕飞宇那里获得相应的证实,但我由小说中足称尖锐的社会批判倾向和政治讽喻意识,尤其是由作家对傅睿这一人物形象的独到性发现与刻画、塑造,所不自觉联想到的,的确是《大师和玛格丽特》和《白痴》。傅睿是家庭条件相当优越的一名外科大夫。由于父亲傅博曾经身为第一医院的党委书记,所以傅睿博士一毕业就顺理成章地进入第一医院的肾外科,成为一名年轻的主刀大夫。但其实,傅睿的人生道路,早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处在各种“被规定”的状态之中。因为母亲寄希望于儿子必须“全面和多能”,所以他最早练习的是二胡。等他刚刚对二胡有了初步的体认,母亲却又让他改练小提琴,后又去改练钢琴。好在傅睿一向顺从,习惯于被安排,所以,“他只管学,从不让别人失望”。同样的道理,看上去很有音乐演奏天赋的傅睿,之所以选择了学医,也与他父亲的强势安排紧密相关。关键的问题是,在傅博强势安排傅睿必须学医的专制行为背后,却也隐藏着他自己的某种难言苦衷。曾经在舰艇上担任过军医的傅博,进入第一医院工作后,所集中负责的,乃是医院里的宣传工作。由于他的能力和认真的态度,医院的宣传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也合乎逻辑地不断被提拔,直到成为医院党委书记。尽管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成功者,但只有他才明白自己的心结所在:“傅博很快就发现了,这座‘医院’里恰恰没有他自己。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呢?如果他沿着医生这条路一路走下去,那该多么好哇。沮丧之余,傅书记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允许大家叫他‘傅书记’,要叫他‘傅大夫’。”但由于他的领导身份,“傅书记”与“傅大夫”折中变成了“老傅”:“老傅再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更沮丧,很挫败。‘老傅’从此成了老傅的病根,类似于高血压、关节炎和支气管炎,拖成了慢性病,过些日子就要犯。”正因为傅博没有能够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医生,而只是成为“老傅”的精神情结,所以习惯于独断专行的他,便把自己没有能够实现的愿望强行托到了儿子傅睿身上。被迫学医后的傅睿求学路上顺风顺水,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还进入了泌尿外科的肾移植专业,成为这一专业具有“国际水准”的领军人物周教授的得意门生。
小说故事真正开始的时间,是2003年“非典”刚刚过去之后。这个时候的傅睿,已经是第一医院泌尿外科肾移植专业的主刀大夫。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原本成活率一直居高不下的这一临床重点专业,不仅接连出现了6例死亡病例,而且这一连串的死亡病例的主刀大夫,正是傅睿。迭遭打击后的傅睿,最惧怕的就是下一个病例的死亡,没想到,却偏偏就应验在了年仅15岁的尿毒症患者田菲身上。因为田菲的尿毒症非常严重,除了透析之外,只有移植换肾这唯一的选择。虽然说田菲格外幸运地等到了特别珍贵的肾源,但在肾移植手术完成后的康复过程中,她还是因为并发症而抢救无效,小小年纪就彻底告别了喧闹的人间。或许与田菲的父亲手术前曾经硬塞给傅睿一把现钞有关,也或许是因为田菲的死亡给父亲造成了太过强烈的刺激,总之,面对着爱女的死亡,一时失去理智的田菲父亲,不管不顾地抢过护士手里的盘子,狠命地砸向主刀大夫傅睿。若非另一位护士小蔡及时冲上去替傅睿挡了一下,倒在地上的就不是小蔡,而是傅睿自己。事实上,只有在读完全篇之后,我们也才能明白,某种意义上,以上的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看作小说的序篇。与本文的标题“‘白痴’抑或先知”这一命题紧密相关的主体部分,可以说从这一场医闹事件发生之后才真正地拉开帷幕。这一方面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主刀大夫傅睿的表现开始变得不那么正常。他先是一个人硬生生地在深夜时分闯进了空无一人的手术室:“温度显示的上方是时间显示,北京时间1:26。1:26,什么意思呢?是下午的一点二十六分还是深夜的一点二十六分呢?傅睿想了很长时间,最终都没能确定。”尽管我们联系下文可以知道确切的时间肯定是在深夜时分,但身为当事人的傅睿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不仅不知道自己回到家的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把手术室的蓝大褂也穿回了家。但其实,傅睿精神方面的不正常征兆,早在2002年4月20日的那个晚上就已经初露端倪。那一天晚上,王敏鹿迫切地想要求欢于傅睿,但却遭到了傅睿身体的坚决拒绝。那一天晚上的“傅睿是心事沉重的样子,特别累,注意力一直不能集中,或者说,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宇宙某一个神奇的维度上”。其实从他相亲时与王敏鹿初次对视时莫名其妙的慌张,就可以发现,他精神方面的异常应该早就有所表现,只不过连同他的妻子王敏鹿,以及家人父母,也都没有察觉而已。
傅睿的精神不正常,表现在很多个方面。比如,他那次被母亲指派去咖啡馆面见感谢见义勇为的护士小蔡。由于在内心里一直把傅睿当作一个典型的“偶实”(偶像实力派的简称),小蔡把傅睿的这次邀约一厢情愿地理解成异性之间的一次约会。傅睿对小蔡脑袋的关注,原本只是关心她的伤势如何,但小蔡却理解为傅睿是在借机以“盘头”的方式调情,所以已经连着两天没洗头的小蔡才会不由自主地躲闪傅睿。正因为相互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关系,所以,等到小蔡准备“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自己的“偶实”度过一段不无浪漫的咖啡馆时光时,不解风情的傅睿却断然起身告辞了。尽管他的突然离开让小蔡很是失望,但小蔡还是更愿意从“偶实”的任性那里寻找相关理由:“他走了,完全符合一个‘偶实’的做派,出现得突然,离开就必须突然。”多少显得有点天真的小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想到,这个时候的傅睿已经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之中。事实上,他们俩在咖啡馆的这一场阴差阳错完全暗合于小说里的一个相关场景。两个人见面后,傅睿率先诚实说明来意:“我母亲让我来看看你。”“这句话小蔡却听不懂了。傅睿大夫的母亲为什么要让他来看望自己呢?小蔡问:‘你母亲是谁?’”“傅睿认真回复说:‘我母亲?当然就是我妈妈。’”听到傅睿的回答,“小蔡笑了。傅睿也笑了。亏了是在咖啡馆,这样的对话要是放在疯人院,那也是可以成立的”。正所谓叙述者无意,解读者有心,虽然毕飞宇安排叙述者发出“这样的对话要是放在疯人院也可以成立”的感叹,很可能是无意的,但因为读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傅睿的精神异常,所以“疯人院”一句,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拥有了某种象征暗示的意味。更进一步说,这一象征暗示,可做二解。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把傅睿理解为“疯人院”里的一员,另一方面,却也未尝不可以把我们正置身于其间的现实社会看作是一个“疯人院”。
当然,促使傅睿精神严重焦虑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包括田菲在内的7个肾移植病例的相继死亡。傅睿却一方面饱受失眠症的残酷折磨,另一方面难辞其咎地思考着自己到底应该为7个病例的相继死亡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傅睿的严重失眠状况:“傅睿对自己的睡眠并没有确凿的把握——睡着了呢还是没睡着呢?也不能确定。傅睿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自己的累。对傅睿来说,每一次睡眠都是一次巨大的消耗,犹如持续了一夜的逃亡。”依循因果关系的逻辑,傅睿之所以会在某个半夜夤夜拜访曾经的肾移植患者老赵,既与他的深夜失眠有关,更与他那难辞其咎的精神焦虑紧密相关。尽管说身为报社副职的老赵在家里曾经一言九鼎,但因为在退休手续尚未正式办理的时候不幸罹患尿毒症并做了肾移植手术,他在家里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终其一生在工作岗位上无所作为的妻子爱秋便成了家庭的主宰者。在家庭权力的更替过程中,老赵虽然也曾经一度心有不甘,但孱弱的病体却还是迫使他最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低下头来。出乎意料的一点是,就在老赵以臣服的姿态全力以赴于身体维护的过程中,主刀大夫傅睿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夤夜登门来访。尽管说在傅睿那里,这一行为极有可能是重度失眠情况下的任性之举,但在老赵的理解中却非同寻常。精神因此而一时处于振作状态中的老赵,遂有两个非常之举。其一是大胆骚扰在家里帮佣的女工明理,将自己的巴掌终于贴在了明理那紧绷着的臀部。其二,由于曾经长时间受到过类似于雷锋、白求恩“只知奉献,未知索取”思维规训的缘故,老赵也把傅睿大夫归类到雷锋、白求恩之列:“老赵不吼叫,也不驰骋。他只是被傅睿感动了,他滋生了传播傅睿与再造傅睿的激动。他一心想把傅睿的故事送到‘象牙塔’(意指所谓网络的大千世界)里去。”料想不到的一点是,老赵所写的表扬文章不仅见诸“象牙塔”,还被刊发在了当地的晚报上。这样一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作为一条辅助性的次要结构线索,老赵之所以能有机地介入小说文本之中,除了傅睿曾经是他的主刀大夫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所写的这篇表扬文章,因其对傅睿个人命运强有力影响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演进与发展。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老赵表扬文章发表在晚报上,傅睿的命运才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峰回路转。就在傅博和闻兰夫妇一心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帮陷身于医患纠纷中的傅睿灭火的时候,第一医院的现任雷书记,却已经自作主张地要主动安排傅睿去参加“骨干培训”了。面对雷书记的如此一番精心安排,原本一心想着要让儿子傅睿成为一名响当当专业大夫的傅博,一时间陷入犹豫不决:“老傅当然知道‘骨干培训’是什么意思;‘名单’是什么意思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小雷,这哪里还是请示,邀功了。老傅一下子陷入了犹豫——该不该把傅睿往‘那条’道路上推呢?”这里所说的“那条”道路,毫无疑问就是走仕途,也即完全复制傅博自己业已成为既往的人生道路。关键问题是,傅博的犹豫不决并没有影响到雷书记的最终决策。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发生在第一医院小会议室里的那一次不欢而散。事实上,关于傅睿到底是“‘白痴’抑或先知”的那种争议性理解,也正肇始于这一次不欢而散的谈话事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身陷医患纠纷中,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因祸得福地进入“名单”被推举去参加“骨干培训”,乃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然而,傅睿给出的态度,却是坚决拒绝,甚至还把烟缸里的烟头和烟灰都一股脑儿地撒向了雷书记的脑袋。如此一种情形,在世俗的理解中,当然就是“白痴”一枚。无独有偶,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傅睿接受培训的时候。进入培训中心后,苦受失眠症折磨的傅睿,几乎每一天晚上都睡不成觉。“傅睿差不多在每天凌晨的五点前后都要出门,游荡,并恍惚,然后,走到走廊的尽头——探头死角的那个位置——拿起拖把,再然后呢,一心一意地拖地。”想不到的是,傅睿如此一种失眠痛苦下不自觉的夜游行为,竟然会被中心主任拿来大做文章。与老赵或者雷书记他们的思维方式一模一样,中心主任做出的决定,也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一下傅睿。虽然傅睿对培训中心的这一次宣传行为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但最终的结果却仍然是无济于事。事实上,也正由于抵抗行为的无济于事,傅睿才会不由自主地在表彰会的现场,生成那样一种自己正在被老傅、雷书记、中心主任他们切除脸皮的超现实幻觉。问题的关键很显然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认识傅睿其人?质言之,他到底是一个“白痴”还是一个先知。不管怎么说,傅睿如此这般看似不通情理的所作所为,促使我联想到的是巴金先生翻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门槛》中的相关段落。尽管说已经有一种声音清楚地告诉女郎,门槛里有着的只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但这位女郎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坚持要走进门槛里去。女郎的坚执行为,所引发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另一种是“‘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在我的理解中,傅睿的反常行为所必然引发的,也极有可能是以上两种极端对立的理解和评价。
除了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坚决反抗之外,傅睿其人另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企图凭借一己之力来拯救这个以欲望的喧嚣和膨胀为显著标志的已然处于堕落状态的现实世界。一个是他对护士小蔡的拯救。小蔡这一条次要结构线索,之所以能够以有机的方式介入傅睿这一条结构主线之中,最关键的一点,恐怕还是要成为傅睿的拯救对象。在一厢情愿地认定傅睿在仕途上将会有很大发展的前提下,身为开发银行副行长的郭鼎荣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巴结傅睿。具体的巴结方式之一,就是不由分说地以“绑架”的方式挟持傅睿去参加“观自在会馆”的一场豪华晚宴。没想到的是,在晚宴现场,傅睿竟然与已经同居在一起的胡海、小蔡不期而遇。因为这一场不期而遇,傅睿坚决认定小蔡已经处于堕落的状态:“小蔡却没有往傅睿的脑袋里冲,她在傅睿的脑袋里往下滑,她堕落了,还在堕落。”既然已经认定小蔡处于堕落的状态,那傅睿的唯一选择,就是想方设法拯救小蔡的灵魂。怎么样拯救呢?傅睿所最终采取的,就是以飞驰的小汽车来催吐小蔡:“傅睿的激进尝试则是拯救灵魂。他要治愈堕落——患者必须呕吐,肮脏的灵魂完全可以伴随着体内的污垢被剔除干净——灵魂不属于任何具体的脏器,这话对,反过来说,灵魂属于所有的脏器。拯救灵魂,靠药物是不行的,移植手术也不行,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辆小汽车。”在如此一种极度疯狂思想的支配下,自然也就有了那一幕带有突出荒诞色彩的帕萨特“灵魂拯救之旅”。
再一个,则是对哥白尼塑像的拯救。在培训中心,有一组中西先贤的塑像。左侧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朱熹、王阳明、汤显祖、蒲松龄、曹雪芹全部来自中国,右侧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奥古斯丁、哥白尼、莎士比亚、培根、笛卡尔、康德、莱布尼茨、牛顿则来自欧洲。某一天,傅睿突然发现这个雕塑群里少了一个人,正是那个堪称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在精神异常的傅睿这里,他看到了哥白尼那窒息的表情:“哥白尼已不能呼吸了,他的瞳孔里全是求助的目光。傅睿企图用他的手指和指甲把哥白尼的鼻孔解救出来,徒劳了。指甲哪里是水泥的对手。”在傅睿的理解中,已经赋予了哥白尼塑像以呼吸和生命,那他接下来的举动,自然也就是采取各种办法拯救哥白尼。不管怎么说,傅睿企图拯救哥白尼塑像的行为,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那个举着长矛,不管不顾地冲向大风车的堂吉诃德。他们的类似行动,尽管在世俗的目光里是极尽愚蠢之能事,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一种神圣意味的存在,却也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承认,2002年4月20日那个晚上之后的傅睿,从表象上看,的确处在了某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认真地揣摩一下第十一章,在被妻子王敏鹿误以为出轨的情况下,傅睿那一大段前言不搭后语的毫无逻辑性可言的自我辩解之词,即不难做出清晰的判断。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傅睿难道真的因此而被看作一位没有丝毫人间烟火味的、不通人情世故的“白痴”吗?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参照屠格涅夫《门槛》中关于那位女郎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方式,我想,毕飞宇笔下的这位傅睿,也同样可以获得“‘白痴’抑或先知”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方式。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正如叙事话语中已经有所暗示的那样(最后一章的临近结尾处,作家写道:“光头确实不是和尚,这个是确凿的,他的谈话甚至涉及了耶稣,当然,还有霍金和荣格,也有王阳明和马云。光头的谈话甚至还涉及了姚明和科比·布莱恩特。”此处对耶稣的专门提及不容忽视),傅睿其实应该被看作一位来到人间的携带有拯救使命的先知。更进一步说,他企图加以拯救的绝不仅仅是小蔡或者哥白尼的水泥塑像,而是已然处于严重堕落状态中的整个世界。不管怎么说,在强调傅睿这一人物形象与批判现代主义之间内在关联性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隐身于其后的作家毕飞宇那凝视世界的忧思目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