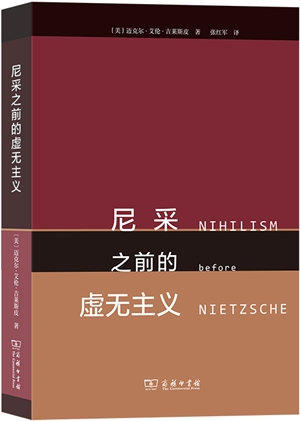
《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 著,商务印书馆
在西方现代性批判话语中,“虚无主义”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我们可以从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德里达、鲍德里亚和瓦蒂莫等众多思想家的著述中发现这一点。但是,正如英国学者沙恩·韦勒所言,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引入现代性讨论的术语的意义,已经因为太多人的界定和使用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含混和神秘,从而正在失去其批判力。问题可能不仅如此。也就是说,如果某位关键思想家对虚无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是错误的,那么他不仅会误导后来关于虚无主义的几乎所有思考,还会把以这一概念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引向一个可怕的方向。美国学者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的著作《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商务印书馆2023年8月版)就在尝试证明,尼采便是这样一位思想家。
在一次名为“欧洲虚无主义”的讲座开头,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虚无主义”一词在尼采之前曾经有过三次明确的使用,即耶可比的哲学使用、让·保罗的诗学使用、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使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海德格尔接下来的谈论几乎完全与这些重要信息无关,他开始悉心分析和批判尼采的虚无主义概念,继而给出自己的虚无主义定义。对海德格尔来说,尼采之前关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谈论似乎无关紧要。吉莱斯皮完全不赞同海德格尔的态度。对吉莱斯皮来说,尼采乃至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本上都是对由耶可比等人最初定义的虚无主义的发展和完成。不仅如此,吉莱斯皮还把这种虚无主义的发生追溯至中世纪末的唯名论革命。
在吉莱斯皮看来,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为基础建立起的现代性城堡,原本是为了抵御中世纪后期出现的唯名论上帝。面对十字军东征失败、黑死病大流行、天主教会大分裂、社会流动性加剧等等变化,唯名论哲学不再像实在论哲学那样让上帝服从于自然秩序或理性法则,而是把上帝规定为超越自然和理性、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与毁灭的全能意志存在。唯名论上帝的全能力量使自然和社会完全变成由个体性的、无关联的存在者组成的一团混乱,让欧洲人漂浮在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世界,陷入一种不断增长的怀疑和恐惧心态,得不到任何安全与幸福的保障。但是,在这种怀疑一切的氛围中,笛卡尔发现那正在怀疑的“我”是确定无疑的,于是就以这个“我”为基础,为现代人建立起一座符合理性法则的城堡,以保护人们免受全能上帝的侵扰。笛卡尔的理性城堡,实际上就是一种普遍科学,人们通过它改造和征服自然世界,从而获得自身的确定和安全。然而,在吉莱斯皮看来,笛卡尔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只是因为他相信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塑造的,从而和唯名论上帝一样具有全能意志:“对笛卡尔来说,去思想,最终就是去意愿。这样,他的基本原理就是意志的自我确认行动,它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事实,即这种意志就像上帝的意志一样,是无限的。”
如果说这种意志观念在笛卡尔的思想中一直隐而不显,与他思想中的理性元素还保持着某种平衡的话,那么在从费希特到尼采的欧洲思想中,它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一进程的关键一步是费希特的绝对唯我主义哲学。费希特认为,“我”作为“绝对之我”的活动是无限的和绝对自由的,但作为“经验之我”即受“非我”限制的“我”的活动又是有限的和不自由的,“我”要想具体实现自己作为“绝对之我”而有的无限性和绝对自由本质,就必须不断设定又消灭“非我”,尽管这样一个设定又消灭的过程永远不会结束,“我”实现自己本质的努力也永远不会停止。耶可比之所以把费希特的绝对唯我主义规定为虚无主义,是因为如果“我”可以设定和消灭任何东西,那么上帝及其代表的真与善就什么东西也不是,而只是虚无。于是,在耶可比那里,虚无主义不是尼采所谓人的衰落和退化的结果,相应也不是人难以支撑上帝的结果,毋宁说是肯定一种绝对的人类意志的后果,这种意志让人类个体成为自然和自然法则的超理性源泉,从而让实在论哲学的理性上帝变得多余,简而言之,让上帝死去。
不过,对费希特本人来说,“绝对之我”还并不等同于人类意志,在其后期思想中,他实际上还称这种绝对之我为“上帝”。把“绝对之我”转换为绝对的人类意志,这是费希特的学生们、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的工作,他们在自己塑造的恶魔英雄中描述了获得这样一种绝对意志的努力,这使得曾经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先驱,后又深受雅克比影响的让·保罗,把他们描述为“诗歌上的虚无主义”。尽管歌德和黑格尔已经严重地担忧这种恶魔式的泰坦主义,尝试限制这种思想,但他们本人也对之非常着迷。他们坚信,魔性只是神性的一个瞬间,浮士德的邪恶最终会被证明是通往至善的途径,而“否定之否定”也是反对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的辩证法。然而,正是他们对这种费希特式意志的利用和转化,使得这种意志开始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屠格涅夫塑造的巴扎洛夫形象,就是对俄国虚无主义者的典型概括。
费希特对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概念也产生了关键影响。不过,叔本华并没有把费希特“绝对之我”的自由意志视为神性意志,而是视为一种主宰一切表象的魔性意志,没有把作为这种意志本质特征的“努力”视为高尚的道德使命,而是视为一种幻觉,意在把人引入一种无目的和无希望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其他,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于是,解决这些使生命无比痛苦的问题的方案,就是“放弃”:要么,像艺术家那样只是静观这个世界及其背后的意志;要么,做一个佛教徒或基督徒那样的禁欲主义者,自觉抑制存在于自己身体中的意志。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观念,启发了尼采的权力意志观念。但是,尼采拒绝叔本华对意志的悲观主义解读,并且把这种悲观主义视为否定生命从而导致上帝之死的虚无主义历史运动的顶点,继而认为作为权力意志象征的狄奥尼索斯神和作为狄奥尼索斯神化身的人类此在能够带着他们所有的悲剧性痛苦,去肯定包括最糟糕时刻在内的生命整体,从而把这种对生命整体的肯定视为克服虚无主义的唯一途径。正如吉莱斯皮所言,尼采对叔本华的逆转,实际上只是对叔本华逆转费希特的再逆转,从而不知不觉间又返回费希特的立场,他和费希特一样赋予了人类个体一种唯名论上帝才有的全能意志,而狄奥尼索斯不过是戴着面具的唯名论上帝。
就这样,吉莱斯皮发现,到尼采为止的西方现代思想史既是显示现代理性的唯意志论基础的历史,又是显示唯名论的全能上帝获得绝对主宰地位的历史,还是按唯名论形象塑造自己的西方现代个体变得越来越任性而可怕的历史,从而也是最初被定义的虚无主义得以完成的历史。于是,吉莱斯皮得出结论,我们与现代性达成妥协或超越现代性的可能,依赖于我们认识和限制唯名论上帝或现代个体的全能意志的能力。带着这个结论,我们会发现,西方现代性批判真的被尼采带向了完全相反因而非常危险的方向。即便是发现了这种危险的海德格尔,也没能真正扭转这一方向,因为正如吉莱斯皮所言,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这个“被他用来作为解决虚无主义问题(作为现代意志哲学的产物)的方案,实际上与早期的全能神性意志概念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他的思想中,存在是一个超越了自然与理性的全能力量,接近于唯名论隐匿的上帝”。